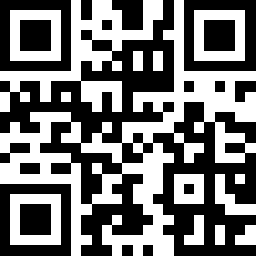肇兴记
一
六月上旬是肇兴的旅行淡季。街头游客稀稀落落,客栈老板们组队去四十里外的黄岗饭醉。
主人爽朗热情,席间歌声不绝。有人终不胜酒力倒下,幸存者们披星戴月赶回寨子,却在景区入口被值班村民拦住。
每位外来人进入肇兴都要购买一百元一张的门票,客栈老板们经常会为被拦而不快,“我们不是外来客,我们是肇兴的建设者。”一轮争执后,面红耳赤的村民放行了他们的SUV。
肇兴依然是黎平旅游的头牌,从新落成的高铁站到寨子只需要十分钟车程,前往县城机场的高速公路也已贯通。经历了各路大师的指点后,地方政府想把这里打造成另一个西山景区,大兴土木让这个古老村寨旧貌换新颜。除了大型停车场,混凝土假山与观赏水车也拔地而起。慕名而来的旅行团和散客在这里寻觅“原生态”风情。
除了几张经常参加歌队演出的熟面孔,寨子里的年轻人并不多。他们要么读书,要么去了沿海打工。“如果要听歌,你应该去三龙、宰荡或者黄岗。”“如果你想看更纯粹的侗寨,往山上走,堂安、纪堂都安静得多。”
客栈老板们熟练地向心有不甘的背包客提供路线建议,但他们依然对肇兴的前景寄予厚望。单是在携程,就可以找到近八十家客栈。从每晚五百元的豪华大床房到二三十元的通铺,肇兴已经可以提供逾千张床位,基本具备作为旅游目的地与集散地的接待能力。
客栈老板只有少数是本地村民,更多的外来客们组成了微信群,但似乎并没有进一步成立行会的计划。毕竟此地的繁荣尚未达到众人预期,高铁的开通也没有带来想象中的汹涌客流。
二
我记不得这是第几次到肇兴。事实上越到后来,我越想逃离这个地方,并不说再见。
这不是一个理想的目的地,但我还是一次次地来。相比黎平和从江县城,肇兴更适合做一个深入南侗腹地的中转站。邻近的两个县城,除了商务宾馆和招待所,你找不到一间像样的客房。
过客居算肇兴最寒酸的客栈之一,它的客房里甚至没有空调。但背包客们总是趋之若鹜,因为这里有一个漂亮的侗族女店员秀花,还有一个生活在传说中的老板青蛙。
秀花平日里也是大歌表演队的主力。她有多漂亮?如果你看过秀花还是少女时的照片,八成也会心动。青蛙有一次告诉我,如果来得及,当年就会把她给娶了。可是青蛙来不及,因为他到肇兴时,秀花就已经结婚生子了。
青蛙是深圳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广东土著。在肇兴的客栈老板圈子里,虽然不是资格最老,却最有公共知名度。在上古的博客时代,他就浪荡成名。后来又给《孤独星球》写黔东南攻略,俨然成了南侗文化的发现者与情怀的推广者。他会带着一帮客栈老板们去黄岗,用侗语和村民对歌,酒酣耳热之际低调地炫耀自己荣誉村民的头衔,也会因为守寨门的村民没认出他而怒飙国骂。
在回大城市闯荡两年后,混成SPG白金会员的青蛙带着一笔投资回到了肇兴,要在山上的堂安做一间精品酒店。酒店名字是我起的,叫“云门”(The Gate Lodge)。
三
预备役精品酒店老板青蛙并没有住在自己的客栈里。回到肇兴后,他住进了另一间客栈,作为寨上成功人士,他已然睡不惯过客居的硬板床。这间弥漫着文艺小清新格调的客栈叫“渡”,他十分积极地安排我也住到此处,然后要我自付房费。
这是渡客栈的第二间店,新任店主是初来乍到的江西小姑娘。自从《中国国家地理》把肇兴评为最美十大古镇,出没肇兴的外来女就有两种,一类是穿冲锋衣的,另一类是打扮得像小野洋子的,她们的共同之处是都管青蛙叫哥。
随着古镇声名日隆,小野洋子数量越来越多。棉麻质地的生活观写在每张脸上,晴天时春风十里,雨季时忧伤逆流成河。
我很喜欢去过客居斜对面的一间客栈。那里有二十元一杯的清咖和安静的小野洋子,吧台上还誊写着汪国真的诗歌。这间客栈的房价要比其他家贵出一截,客流以内地文艺中年为主,尽管去几次都碰到东北大叔大妈,但BGM一般是肖邦的降E大调华丽大圆舞曲,一种大型当代生活。
相比下,渡客栈小野洋子浓度还不够高,价格也一直上不去。
若是老板妈妈看店,小野洋子浓度几乎就是零下了。
四
早几年来肇兴,我常到海湘吃饭。海湘老板是比较早一拨来侗寨淘金的上海人,店里有汤力水,会做不是那么难吃的意大利面。
老板告诉过我很多故事,他记性和我差不多,所以隔段日子再去就会再讲一遍,我也当作新故事来听。那时我住在海湘楼上的客房。侗族建筑以木楼居多,隔音差。当年游客很多是穿冲锋衣的,他们常一个人来,两个人住。大白天就在房间里搞得地动山摇,我就下楼找老板抽烟,听他抱怨经营的不易。
我已经两年没见过老板了,老板好像姓张。最近一次到肇兴,海湘已经变成了一家有巨大霓虹灯招牌的慢摇酒吧,老张不见了。
我在行走侗疆的近十年里,一次又一次地路过肇兴。我并不爱这个地方,却总是沉迷于此。
直到今天我才想写一点什么,这真是一个让人悲伤的谜语。

![[微笑] [微笑]](https://face.t.sinajs.cn/t4/appstyle/expression/ext/normal/e3/2018new_weixioa02_org.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