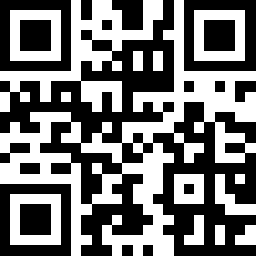远离那个苦苦追求你的人
2015年5月27日 13:59
阅读 73378

题记:
人生一大悲剧,就是与追求自己多年的人结为伴侣。
如果你真的爱她,她不爱你,那么你能给她最好的礼物,就是停止追求,作她良善的朋友。
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一、“乡下人”沈从文的痴恋
18岁的张兆和皮肤黝黑,留着短发,神采飞扬的在操场上吹口琴,青春的活力与不羁深深打动了“乡下人”沈从文。合肥九如巷张家的三小姐,通晓四书五经和西方典籍,能说一口比苏州话还溜的英文,对戏曲诗文都有造诣。唯独对人世间的男女欢爱,完全懵然无知。
他对她一见钟情,狂热的追求,一篇篇火热的情书,不吝惜世间任何卑微的字句:
“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的。”
这样的情书,张兆和每天都要接到十几封,后来发展到每天几十封。所有人都知道,沈从文爱张兆和爱得发疯了,展现出了他乡下人的“蛮劲”,运用全部才华长篇大论写情书,已类似于攻营拔寨。或许在沈从文眼中,张兆和不仅是他爱慕的女子,也是大都市现代文明的象征,他从遥远的湘西走来,带着满身的土气,但才华和一支笔是他最好的利器,他有自信一定最终获得胜利。
今天,读沈从文给张兆和的情书,大半都是一个男子对自己狂热爱情的表白,思念之情的抒发,诗兴勃发的兴奋,再往深里读,是因有了这份激情后自我陶醉的自恋。其实,那些情书的对象,可以不是张兆和,可以换成任何人——在所有让后世感动唏嘘的“爱情诗篇”里,张兆和的面目从来都是模糊一片。
首先,他想得到她,为此不惜一切:
“我曾做过可笑的努力,极力去和别的人要好,等到别人崇拜我,愿意做我的奴隶时我才明白,我不是一个首领,用不着别的女人用奴隶的心来服侍我,但我却愿意做奴隶,献上自己的心,给我爱的人。我说我很顽固地爱你,这种话到现在还不能用别的话来代替,就因为这是我的奴性。”
——你可曾见过如此咄咄逼人趾高气昂的“奴隶”?向来温和的沈从文自己或许都不会发现,字里行间,一种强烈的逼迫感向人压来,一种征服者的态度以“奴隶”的字眼摆了出来。是霸道还是温柔,是欲望还是体恤,一个从未有过恋爱经历的18岁姑娘怎么得看得出来呢?
在与她结合之后,他继续他狂热的幻想,并且,连他最骄傲的写作,都受了滋养,这又给了他更深的骄傲:
“我有了你,我相信这一生还会写得出许多更好的文章!有了爱,有了幸福,分给别人些爱与幸福,便自然而然会写得出好文章的。对于这些文章我不觉得骄傲,因为等于全是你的。没有你,也就没有这些文章了。”
“我今天离开你一个礼拜了。日子在旅行人看来真不快,因为这一礼拜来,我不为车子所苦,不为寒冷所苦,不为饮食马虎所苦,可是想你可太苦了。”
“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有了你在我心上,我不拘做什么皆不吓怕了。你还料不到你给了我多少力气和多少勇气。同时你这个人也还不很知道我如何爱你的。想到这里我有点小小不平。”
看,虽说是写给张兆和的情书,可你可曾看过张兆和的影子?里面尽是沈从文自己的羁旅之苦、思念之苦、写作进步、勇气增长……他不过是找个人来倾吐。
便是那首最著名的:“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说的还是他自己。
这场疯狂的“爱情表演”感动了周围的人,也感动了沈从文自己,他深陷其中,真诚的相信自己爱张兆和爱到了骨髓里,自觉此情感天动地,他还找到张兆和的室友王华莲代为传音,谈及对张兆和的刻骨爱恋,不禁伤心痛哭,表示自己若不成功便有寻死之意。王华莲对此却殊无好感,她不能理解一个男人如此死乞白赖痛哭流涕的“爱情”,张兆和也一样。她从一开始就对这种“行为艺术”非常反感。
但校长胡适介入了,他与张兆和面谈,大夸沈从文是天才,是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当听说张兆和“顽固的不爱沈从文”时,胡适“为沈叹了一气,说是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人人应该帮助他,使他有发展的机会!”——这样的语气,像极了当年延安时期动员女性嫁给革命老干部吧?这个逻辑近乎无赖,等于将爱情等同于一种利益,因某人有了某种功勋或才能,就该判给他所欲求的女子。至于女子的意愿,是全然不在考虑之列的。

(胡适与其妻江东秀,包办的婚姻很难谈得上幸福,江曾经举刀威胁胡适拒绝离婚。)
可叹留学美国、新文化运动的干将胡适,在这个问题上的认知依然带有浓厚的男权印记。一切都以男子的需要为评判标准,女子在这里只是一个物化的对象。在随后写给沈从文的信中,胡适说:“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此人太年轻,生活经验太少……故能拒人自喜。” 一个从未谈过恋爱的年轻姑娘,拒绝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就要被扣上“拒人自喜”的帽子,并且来自于大名鼎鼎的校长胡适,口吻又是何等蔑视——“一个小女子”,就该知道,张兆和所面对的,是怎样一种恶劣的情境了。
从胡适家里出来,张兆和在日记里写道:
“胡先生只知道爱是可贵的,以为只要是诚意的,就应当接受。他把事情想简单了,被爱者如果也爱他,是甘愿的接受,那当然没话说。如果被爱者不爱这献上爱的人,而光只因他爱的诚挚,就勉强接受了它,这认为的非由良心互应的有恒结合,不单不是幸福的设计,终会酿成更大的麻烦与苦恼。”这段话,或许可以看做日后二人感情的谶语。
二、“冷漠少女”张兆和
禁不住周围人的各种劝说,张兆和动摇了:“不管他的热情是真挚的,还是用文字装点的,我总像有我自己做错了一件什么事,因而陷他人于不幸中的难过。”聪明的张兆和其实已隐约察觉到了这疯狂爱情的“装点”成分,但出身名门世家,自幼受过良好教育的张兆和理性的认为,再这样下去自己在道德上恐怕要陷入一种不义。于是,她妥协了,她答应了,她嫁了一个自己根本不爱的人。
我在写爱尔兰著名女性毛特•冈的时候曾说过,“爱情并非源于感动,不能屈从于任何名气或光环,也不能为了迎合大众而作任何决定。……经济、地位、声名都不能左右一个独立女性的意志。”便是在看到了很多被迫答应求爱的情况有感而发。很遗憾,张兆和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她没有毛特•冈那样坚强独立的意志,也不可能像前者拒绝叶芝那样拒绝沈从文,她甚至没来得及仔细思考人生,更不要说剖析自己,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她本是一个性格冲淡的女孩,尽管看了许多文学作品,丘比特的箭却从未将她射中。甚至于,对于爱本身,她都是高度怀疑的:
“我是一个庸庸的女孩,我不懂得什么是爱——那诗人小说家在书中低徊悱恻赞美着的爱!以我的一双肉眼,我在我环境中翻看着,偶然在父母、姊妹、朋友间,是感到了刹那间类似所谓爱的存在,但那只是刹那的,有如电光之一闪,爱的一现之后,又是雨暴风狂雷鸣霾布的悲惨可怖的世界了。我一直怀疑着这“爱”字的存在。”
在优等生张兆和心中,不仅爱是可疑的,就连对人世间的情感她也不敢相信,她曾问过姐姐允和:“人与人之间除了相互利用之外,还有什么?”显然,这个“庸庸的女孩”才是她的本来面目,而这些,激情四溢的沈从文从未真正深入探究过,他已经被自己一厢情愿的想象完全遮蔽了双眼。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愿意当“奴仆”伺候终生的这位小姐究竟是个怎样的人,有着怎样的灵魂。盲目的热情遇上懵懂的无知,想象代替了了解,这场姻缘在一开始,就注定了悲剧的性质。

(沈从文张兆和夫妇、长子龙朱及沈从文的九妹。)
在日后漫长的岁月里,沈从文数次感受到了张兆和的“无情”,兵荒马乱的抗战岁月,他逃离沦陷了的北平独走武昌,张兆和带着两个孩子在北平生活得怡然自得,迟迟不愿去内地与沈从文团聚,使得沈从文干脆就写信给她说明:若她有其他的幸福,他决不阻拦,而且明白的说他感觉这样的分离比相聚更让张兆和过得开心。似乎对张兆和来说,沈从文这个人唯一让她感兴趣的就是他的书信,以至于沈从文干脆负气的问“你爱的是我这个人还是我的信”?
很多人认为沈从文与张兆和婚姻的不和源于张兆和的冷漠;有些人则出于“和稀泥”和“粉饰太平”的心态,说二人的婚姻最终还是“幸福的”;也有些人客观的看二人的全部历程,感叹这场婚姻很难说是幸或不幸……无论是哪一种说法,似乎都站在大作家沈从文的立场上来看问题,而女主角张兆和,似乎只被定型为沈从文狂热追求的爱人和婚姻中冷漠的妻子。——女性总是在这样的场合里,扮演被指责和被审判的角色,鲜少有人关注她们的内心世界,更无从体会她们的不安与悲苦。张兆和如是,陆小曼如是,王映霞如是,连普希金的妻子,亦如是。对大众来说,她们只是“大作家的妻子”,而已。

(合肥九如巷张家四姐妹,右上为张兆和。)
张兆和当然从未爱过沈从文,这个生长在复杂大家庭里的姑娘,兄弟姐妹众多,她不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自幼“没有人娇宠她,也没有人会为她心痛流泪。” 时常被母亲锁在房间里,只留一串糖葫芦;家庭教师和保姆都极严苛,前者还时而拿木尺打她的掌心;家人都说她性格古怪,喜欢毁坏娃娃,曾用小凳子把泥娃娃砸得粉碎,将布娃娃撕成碎布,用剪刀剪掉橡皮娃娃的头……这明显是一个缺乏关爱的孩子,自幼的被忽视和爱的匮乏造成她日后对人世间的情感普遍怀疑。也许若有人从一开始能发现这些,慢慢接近她的内心,一点点探究她心灵深处的世界,或许还会让她敞开心扉,渐渐修补她内心中寒冷孤峭的世界。
本来沈从文或许是最合适的那个人,但这些,沈从文并不知晓,也从没认真想起去探究,他只是心心念念“顽固”的爱着一个他想象中的女子,并为这女子的无情和冷漠而伤心。他以张兆和的外貌为原型,创作了自己一系列小说中的女子形象,包括《边城》里的翠翠,可那些女子都只徒具张兆和的外表,而全无她的灵魂——这也是他根本不了解的。不能否认他对张兆和的爱一片赤诚,但却建立在他完全不了解对方的基础上,这样一厢情愿的爱,给的真是张兆和本人吗?
终其一生,张兆和鲜少对沈从文表达过思念,更没有几句热辣的情话,倒是在她早年的日记里,分明看得到她当初对沈从文的态度:“永远也不会爱”。在沈从文死后,张兆和整理他遗稿的时候感叹道:“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到最后,张兆和对沈从文的评价,也只是一个“善良”。 狂热爱了一辈子,生活在一起一辈子,盖棺论定时,被发的是一张好人卡。这是谁的错呢?
三、苦恋的盲目与悲剧
归根结底,沈从文和许许多多尘世间的追求者一样(特别是男性追求者最易如此),都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没有真正“看见”追求的对象,他们根本不知道对方究竟是怎样活生生的一个人。无论情话说得多么感天动地,爱得如何奋不顾身,那只是一个人的单恋,他们想的都只是“得到”,并且为这“得到”的欲念发疯,将所欲求的对象无限美化,却忽视了所爱的真实存在。
有人说,世间的诸多所谓爱情,大半是源于误会。但事实上,那些相爱至深的伴侣,却恰恰只能是源于了解,之后才是两心相通与共鸣的欣喜。就如与张沈同时期的杨绛和钱钟书,二人一见钟情,彼此中意,完全没有谁追求谁这一说法,而世间那些最美满的婚姻,总是有着类似的历程。
在这一点上,冰雪聪明的才女林徽因看得非常透彻,当年她拒绝了痴恋她的徐志摩,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世都被无数人惋惜,但晚年的林徽因对儿子梁从诫说:“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
是的,爱必须真实,建立在虚幻基础上的任何事物都善变而不可信。真正的爱情应该是因为理解而相爱,只有当爱上的是一个真实而具体的对象而非幻象时,基石才会建立得牢固,摩天大厦才不会坍塌。空中楼阁的确很美丽,但那没法伫立在大地上。爱拒绝想象。
常见到有人炫耀自己当初的被追求,固然说明自身的魅力,有人欣赏喜爱总胜过无人问津。但被追求者追到,总是被挑选的结果,主动权在对方那里,你的自由意志又在何方?他当初追求你越辛苦,只能说明你当初有多么的不中意他,仅此而已。
和一个不爱,只是被其诚挚追求而感动的人结合,对于寻求安全感的人来说,也许是个安稳的归宿,但内心里潜在的不甘会以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张兆和对沈从文的“冷漠”;对追求爱情的人来说,则是一生的噩梦。即便从追求者的角度而言,这也是一场“惨胜”:形式上完满,而内心中永远惶恐。岁月久了,生出来的是不满。心是不会骗人的,爱或不爱,是爱还是感动,大家都明白。
所以,远离那个苦苦追求你多年的人,你根本不爱他/她。你不会给一个你爱的人那么辛苦追求你的机会。不只是现在,以后也不会爱。爱情是多么强烈的情感,怎么还会存在“爱上了却没察觉”的情况?在漫长的追求过程中,一个人可以对另一个人加诸太多不符合事实的想象,这些想象会成为日后在一起时的处处暗礁;一方由于追求长时间处于极其卑微的位置,而另一方则习惯性的高高在上,这并不符合爱情和婚姻平等结合的规则,天平失去平衡,两个人心中都会有所不甘。看看身边,是不是都有些苦苦追求多年,最终结合却很快分崩离析的例子?
和一个不爱的人共度一生,不是不可以,而是要做好准备,不要幻想日久生情,日久生的是亲情,不是爱情。没有爱情,对于一些向往爱情的人来说,总是终身遗憾的事。
至于沈从文和张兆和,也许正如周作人所说:“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或许沈从文到死依然觉得自己深爱着张兆和,而他当然不会知道,这种盲目的爱,早让他在心中塑了一尊琅琊玉洞中的“神仙姐姐”(参见金庸小说《天龙八部》),当然,那绝对不是张兆和。

(沈从文与张兆和仅有的几张年轻时的合影里,张兆和常是双臂紧抱,和沈从文保持一定距离。)
码字辛苦,本文系作者个人版权所有,欢迎转发,任何媒体转载需与作者本人联系获得授权,否则视为侵权行为。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