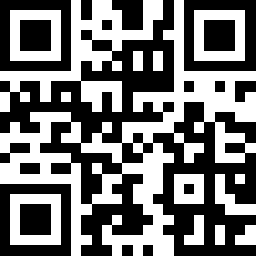孙新华:湄潭贡献还是湄潭教训?——与周其仁教授商榷
“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最早由贵州湄潭县进行试验,并在后来推向全国农村。周其仁教授是这一试验的主要参与者、总结者和宣传者,应该也是使这一地方试验能够推向全国的重要推动者。近来,周教授又在《经济观察报》开设的“城乡中国系列评论”栏目中大谈特谈湄潭试验的贡献。在他的论述中,湄潭经验于国于民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大好事,但是笔者在全国农村调查所了解到的情况却非如此,甚至湄潭的农民也并不认同这一试验。问题到底出在哪?
一、周其仁眼中的湄潭贡献
1987年,湄潭作为全国首批9个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开始试验以“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为核心内容的土地制度改革。主要做法是,在土地承包期内,无论是因为结婚、生子等带来的人口增加,还是由于去世、出嫁等导致的人口减少,都不再进行土地调整,稳定每个人口与土地的对应关系。与禁止土地承包期内进行土地调整同时进行的是,最大限度地延长承包期,由1980年代初的20年延长到1997年的50年。两者结合起来,就使“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在长期得以实现。这就是后来在全国推行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和“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制度蓝本。在周其仁看来,这种制度蓝本具有以下贡献:
第一、化解了土地继续细碎化,提高了农民投资土地的积极性。周其仁认为,如果继续按照“增人增地、减人减地”进行土地调整,每增加一个人就要从原有地块中切除一部分分给他,这样就会进一步加剧土地的细碎化,随着新增人口的增多,土地就会无限细碎化。而频繁地调整土地也不利于激发农民投资土地的积极性,反而会造成掠夺性耕种。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则稳定了承包关系,从而缓解了土地细碎化问题,也有利于农民更好地向土地投资。
第二、彻底告别了集体经济,有效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权利。在周其仁看来,“集体是模糊之源”,从而使“‘集体’与‘农户’的发包、承包关系,一直剪不断、理还乱”,这是“集体”侵犯农民的权利的根源(《土地承包,意犹未尽》)。而通过“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长期化,从而固化了土地承包关系,实际上使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实现虚化,而农民的承包权得到强化,用周其仁的话说就是承包权的“强度”大大加强。这就有效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权利。
第三、有利于农村人口从土地上转移出去,提高了非农收入和城镇化率。正如周其仁所说“先在耕地上划下一道不可再细分的警戒线,人们或可被逼着向非耕地资源找出路。本地资源不够?那就向外地、向远方找。”这样,“把新增劳力逼出耕地以外”(《湄潭的贡献》),从而推动他们转向城镇从事非农就业,既有利于增加非农收入又可推动城镇化。
第四、减缓了人口增速,有利于控制人口增长。周其仁看到,在“增人增地”的情况下,“新增人口有权增地……刺激各家增加人口,因为那是重新分地的筹码”,而“谁家人口少了就吃亏,不利计划生育”。在“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实施后,“湄潭的自然人口生育率下降显著,比全省和全国的都低”(《湄潭的贡献》)。
为了让大家认识湄潭的贡献,周其仁在多篇文章中将以上几条翻来覆去地宣讲,似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已经完美至极。一般人不去深究,还真可能就被他的宣讲忽悠过去了。明眼人则不会,而对此最有发言权的明眼人就是广大农民群众,因为正是他们默默承受着这一制度带来的苦与泪、痛与悲。他们虽然不常语于外人,当然也很少有这种机会,但常到农村调查的人都知道,农民在不经意间便会流露出对“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抱怨,而且往往是义愤填膺、滔滔不绝。因为正是周其仁眼中的完美制度给他们带来了不尽的麻烦和苦楚。下面,笔者就结合自己在农村的调研所得,来为各位看官揭开周其仁教授不曾言说的另一面。
二、化解还是固化了土地细碎化?
先来看土地细碎化问题。周其仁说,“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化解了土地继续细碎化问题,这一说法看似有点儿道理的,实则很片面,因为土地调整时期的“大调整”可以克服土地无限细碎化问题,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不仅没有化解反而固化了既有的土地细碎化,而且是长久固化。
首先,来看周其仁看似有点儿道理的地方。在“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实施前,各地包括湄潭都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的土地调整政策,其中比较常见的方式是“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小调整”一般指减人的农户把多出的土地补给增人的农户,往往是出地的农户将最差的田块或者从中切除一块给进地的农户,如果是从原有的田块中切出一块确实会增加田埂系数,使土地更加细碎化。但是由于“大调整”的存在,这种进一步的细碎化实际上是可以克服的,因为“大调整”是将集体的所有土地集中起来按照当时的人口重新分配土地。所以,在真正实施“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的地方,根本不会出现周其仁所说的土地无限细碎化下去的可能。
其次,再来看周其仁隐而不讲的固化土地细碎化问题。对农村有所了解的都知道,在分田到户之初,为了做到公平,绝大部分地区的农村都是按照土地的远近、肥瘦搭配分田,从而形成了“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且地块分散在至少七、八上十处的格局。这种分法在分田到户初期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在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土地的远近、肥瘦对农户的经营和收入的影响确实很大,尤其是因为当时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土地,他们对土地的细微差别都非常在乎。而由于近十年来基础设施尤其是沟渠路的改善和生物、化学技术的大量采用,使田块之间的差别逐渐缩小,且随着务农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相对下降,农户对田块之间的细微差异也相对淡然,这个时候他们最心烦的恰是土地的细碎化带来的不便,这在南方农村表现的尤为明显。土地的细碎化不仅大大增加了农户的耕作成本,也不利于农业机械等先进技术的采用和投入,亦阻碍了土地流转和经营规模的扩大。
本来我国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已经赋予了集体进行调地以解决土地细碎化的权利,比如集体在改善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将每户的土地都集中在一起,甚至可以将规模经营户流转的土地都集中在一起,从而化解农业经营中的细碎化困境。但是由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严重虚化了集体调地的权利,并强化了每个人口与土地的对应关系,这样就固化了分田到户时的土地细碎化格局,而且长久不得改变。此时的集体虽然很难通过干涉承包权侵害农户权利,也无法通过调整土地来克服土地的细碎化问题了。当然,有人可能会提出农民可以通过相互调地来解决细碎化问题,但是由于土地过于分散和交易成本过高,这种解决之道实难真正奏效,这也是为什么全国绝大多数农民都仍在艰难忍受着土地细碎化之苦而无法排解。而这一切都是拜周其仁极力推崇的湄潭贡献所赐:本来确是想化解土地细碎化,然而实际上却在长期固化了土地细碎化。
三、虚化集体权利是好事吗?
这就牵涉到周其仁所说的湄潭试验对虚化集体权利的贡献。对周其仁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他极力主张农村土地私有化。他极力推崇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或许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只是碍于《宪法》规定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而无法彻底实现。尽管通过“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集体权利已经成为一个摆设,而农户的土地权利已然“准私有化”,但是周其仁教授还是不甘心。且看他怎么说的,“想想看,不需要跨农户、跨时期的土地再分配,真正实现了农户承包经营的长期不变,让有偿、出价、合约机制来处理农村人口与土地的结合方式,还要“集体”那个劳什子作甚用?”“劳什子”是什么意思呢?细查,原来是方言中对厌恶之物的蔑呼。以此可见,周其仁对集体是何等地讨厌,怪不得急欲除之而后快!
但是,村集体真的一无是处吗?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很多一家一户“办不好或不好办”的公共事业都要靠村集体来完成,更何况曾经参与起草“中央1号文件”的周教授?1986年的“中央1号文件”就明确指出,集体“统”的层次存在的必要性就是,一些事情是“一家一户办不好或不好办的事”,这些职能应该由集体经营层次来承担,比如沟、渠、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修缮等。农村很多基础设施的修缮都需要超越单个家庭的范围,比如水利设施、田间道路等都很难由单家独户承担。既然是超越家庭之上的公共行动,就自然可能遇到钉子户的问题。比如建设或修缮基础设施时需要占地,有些农户可能会出于各种理由不让占用自家的承包地,如果无法克服这样的钉子户就无法完成公共事业。
在集体有一定权利的时候,则可以通过调整土地使大家平摊被占土地或者从机动地中划出一部分对涉及农户进行补偿,从而化解难题。但在“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实施后,农户的权利已经被刚性化,而集体的权利则被严重虚化,集体再无权利干涉农民的土地也不再拥有机动地了。此时,任何一个钉子户就可以将对绝大多数农户都有利的公共事业废止,因为按照规定它的权利是得到保护的,而集体虽是所有者也没有权利干涉农户的承包权。尤其是农民日益分化和不在村农户大量出现的当下,这种困境出现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有承包地但不种地的农户与务农户的利益诉求完全不同,他们也不再关心农业生产,因此如果其中有些人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或者故意阻拦,基础设施的建设或修缮肯定会陷入僵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贺雪峰教授认为“给农民更多的土地权利,其结果可能恰恰会损害农民的利益”,即少数拥有更多土地权利的农民可能对多数农民的利益造成损害。自命为九亿农民代言的经济学家,周教授不至于连这种经济学教材都讲过的“反公地悲剧”都理解不了吧?
这就是周其仁主张的虚化集体权利的结果。有时集体确实会侵害到农民的权利和利益,但理性的人都知道,相对于集体能做的积极的事情,这种负面的后果毕竟是少数。而周其仁为了不让集体做坏事,主张干脆把集体取缔掉算了。这岂不是因噎废食!
四、难道农民进城是逼出来的?
如果说周其仁以上两点主张是因小失大的话,那么他有关“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会推动农民进城上的论证更是“一条经典的奇谈怪论”。前面我们简单展示了他的论证逻辑,下面让我们稍作展开来看看它到底“奇”在哪里,“怪”在何处吧。
从前面已经可以看出,周其仁论证的核心在于“逼”农民离开土地进城求生。我们不妨再来温习下他的高谈阔论,“先在耕地上划下一道不可再细分的警戒线,人们或可被逼着向非耕地资源找出路。本地资源不够?那就向外地、向远方找。横竖一鸡死、一鸡鸣,经济结构之变,缺了背水一战的动力,是永远搞不起来的。”“把新增劳力逼出耕地以外,不见得一定就是死路和穷路,搞得好,也可以是活路和富路”(《湄潭的贡献》),同样,我们反过来讲也是成立的,即也不见得一定就是活路和富路,搞不好,也可以是死路和穷路。所以,他也承认“究竟转得过去还是转不过去,非经过试验,谁也没把握给予回答”(《拖泥带水的新体制》)。
从中得知,周其仁的设计是通过“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制度将农村新增劳动力逼到城镇去,至于他们能不能进得了城周其仁就没有把握了。而正是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周其仁设计的制度却帮那些农村新增劳动力做出了“背水一战”的决定,“横竖一鸡死、一鸡鸣”。反正,有什么不良后果也不需要周教授来承担。但请问周教授,难道中国的城镇化到了非要逼农民进城的地步了吗?既然要逼农民进城,何不模仿英国的“圈地运动”呢?显然这是有极大风险的,那么难道“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将农村新增劳动力逼出去就没有风险吗?这些劳动力在年轻的时候自然是可以进城务工的,但是进城务工不等于能够在城安家。他们中的大多数到一定年龄后仍无法在城市安家,而又失去了务工的年龄优势,这时他们若有承包地自然可以顺利返乡务农。但是他们却自出生就没有分到土地,他们返乡就没有那么顺利甚至还会遇到麻烦,留在城里没干头,返乡又没想头,这个时候他们的生活就会非常艰难。这样他们的生活就没有安全感、稳定感,再想到同样作为村集体成员在土地上却分配不均,他们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感就会徒然增加。而这些无地的农民又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因此就为整个社会的稳定埋下了重大隐患。而这种隐患在周期性的金融危机下很容易就会转化为现实的威胁。
因此,借助“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来逼农民进城实在是奇谈怪论,对国家、社会和农民都是百害而无一利。近期,周其仁又在热捧“农地农房入市”,不知他是不是觉得逼农民进城光从耕地着手还不够,还要将农民的宅基地和房子都卖掉才行?正常的农民进城应该是随经济发展而来的一个自然过程,而不是靠将农民赶出土地逼着他们进城。相反,让他们在农村拥有一份“进可攻、退可守”的保障,则会使我国的城镇化更加稳健和顺畅。
至于周其仁所讲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对控制人口的作用就更不用说了。这个作用可能会有一点,但几乎是微乎其微。对农村生育有所了解人的都知道,很少有农民会为了多分一个人的地而多一个孩儿,因为一个孩子的抚养成本远大于一份地带来的收入;同样,也很少有农民会因为生了孩子分不到地而少生孩子或不生孩子。近三十年来,我国农村的人口出生率普遍都在下降,但主要是计划生育工作以及教育、结婚、建房等方面的成本增高所致,贵州湄潭也不例外。而周其仁却把“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对人口下降的微弱作用进行放大,并抬出来为自己的主张正名,也足见其已“黔驴技穷”了。
五、是否符合大多数农民的意愿?
一个制度是不是好制度,关键还是当事人说了算,因为“老百姓心里有杆秤”。似乎周其仁教授也不否认这一点,他在1989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中曾说“制度要成为人们经济行为的规范,必须以多数当事人在事实上能够接受为前提,否则,再好的制度设计也会因为高昂得无法支付的运转费用而永远束之高阁”。在同一篇报告中,为了验证“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可接受性,他论证到试验区对三个村的15名干部和510名农民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46.7%的干部和64.7%的农民赞成‘人口增减不调整土地’”(《湄潭:一个传统农区的土地制度变迁》)。这里姑且不论试验区当时的调查是否科学和受访对象的意愿是否真实(一般的试验区为了论证自己的试验,往往会千方百计地为自己找到支持的证据),权当真实反映了事实情况吧。但是试验之初的农民支持并不代表制度实施后农民仍然支持。但纵览周其仁近期论述“湄潭贡献”的大作却丝毫不提现在农民的意愿如何。不知他是确实不知,还是有意隐瞒?
那就让我们来告诉周教授吧。首先来说下我调查中的一个故事吧,今年上半年我在安徽繁昌县驻村调查三个月,其间我与一位60多岁、非常有威望的老村民组长聊起“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他对此很有意见,我说这个制度主要是几位学者提倡的,他拍桌而起怒发冲冠地喝道“不管是谁提倡的,他只要站在我面前,我就跟他干一架,打死他我也不怕,农民都会支持我”。当时,我很震撼,没想到农民竟会如此反感这个制度。那么他的这个态度能代表多少农民的想法呢?据我所知,他的想法在当地具有极强的代表性,那么放在更大范围呢?因为目前还没有全国的统计数据,我们无从得知。
幸运的是,周其仁的老搭档、也曾参与湄潭试验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刘守英研究员这二十多年来一直跟踪湄潭的改革,他在近两年的调查中统计了农民的意愿,也许可以参考。他在全县抽查了500个农户,统计结果显示:“尽管这一制度在湄潭已实施了24年,农民对土地再调整的意愿仍然强烈。93%的被调查者同意按人口进行土地再分配,89%和90%的人认为嫁入村里的人口和新出生的孩子也应该分得土地,54%的人认为逝者的土地应交回村里重新分配,只有41%人同意可由家人继承。”(《贵州湄潭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24年的效果与启示》,《中国乡村发现》2012年04期)
这应该已经比较能够说明问题了,因为这一统计结果恰恰是来自“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发源地同时也是周其仁一直津津乐道的湄潭。至此,我们也完全可以有底气地说,周其仁所力推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是不得人心的。尽管如此它却没有被“束之高阁”,反而被推向了全国,只能说,这是周其仁的大幸,却是农民的不幸。
综上所述,我们会发现,周其仁所宣扬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和现实中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实在是大相径庭,甚至是南辕北辙。周其仁眼中的“湄潭贡献”,现实中却是“湄潭教训”。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原因可能在于,周其仁教授至今还在固守着80年代末为湄潭试验论证时的思维,并利用当时在湄潭的调研来论证其合理性,对于当下广大农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期所盼却视而不见、置若罔闻,更可能的情况是他确实不曾了解。因此,最后还是奉劝周其仁教授一句,21世纪都过了十几年了,别老拿自己上世纪80年代的调查来说事了。真想为九亿农民代言,还是先到现实的农村听听农民的真实呼声吧!
2014年9月13日初稿
2014年9月19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