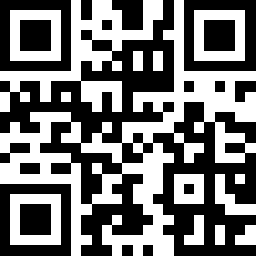《相见时难》
在市图书馆前台排队办理借书证更新业务的时候,她打开手机看了一下时间,快11点了,她约好了婆婆和妮妮中午十二点在必胜客碰头的。队伍前面还有两个人,应该来得及。
生完妮妮之后她就没有来过市图书馆了。离家里有点远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她早就没把心思放工作上了。老公单位忙,婆婆虽然过来帮忙一起照顾妮妮,可老年人的身体毕竟当不得年轻人,又不是自己亲妈,情绪上生活上还要她花好些心思去体贴和照顾,真是一刻钟都放松不下来。这次不是领导吩咐她写一份材料中必须要查一个资料,她估计这辈子也不会来图书馆来了。就连借书证,她都找了好久才找到,一看,早就过期了。
结婚,生孩子。孩子可爱,老公拿出来不丢人,自己的模样稍加修饰,还能赚得一句“跟读研究生时候一样”——管它真心假意,反正这样的日子,她挺满足。日子还能怎么样过呢?她想不出来。只有在片刻,在非常非常偶然的片刻,她会有一种不知自己在干什么,不知道自己是谁的错乱感。
比如正在排队的这一刻,没有妮妮需要她照顾,没有婆婆跟她说这说那,就她自己一个人,站在前后都是陌生人的队伍里,她就会升出那种错乱感:这是我该在的地方吗?为什么这个环境,这些低着头办事的、看手机的、低声细语的陌生人看起来都不像是真实的?那一刻,她感觉自己对周围的环境和人而言,就像透明的空气一样,是根本不被看见的存在。
这种感觉,也会出现在和丈夫在一起的时候。前些天晚上,他像往常一样侧躺着从后面进入她身体,可她感觉他就像是进入任何一个女人的身体一样,这个身体的主人是谁,对他而言根本就不重要。她自己身体的感觉,也和任何一个被插入的女人一样,仅仅只是器官摩擦带来的短暂激动,和她的内心,并没有什么关系。
喂,你好!对,是我。我在上海。
一个男人接电话的声音忽然从队伍后面响了起来,扰乱了她刚才在脑海中浮现的那幅有些令人沮丧的画面,也打破了图书馆这片公共空间里被刻意保持的安静。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通常都会自觉地停下手中事情,以行注目礼的方式向声音的主人表达一个有公德意识的大都市人应有的抗议。接电话的男子想必也是意识到了接通电话那一刻自己的音量有些高,马上压低了声音,自觉地离开了正在排的队伍,一步步向不远的出口处走去。
队伍又恢复了安静,看手机的接着看手机,低声细语的接着低声细语。
只有她,觉得有什么不对。
那个男人不是上海人,她听出来了,虽然他说的是普通话。上海人说普通话和外地人也是不一样的。那男人的普通话里带有她熟悉的一个地方的独特尾音。还有他的发声方式和部位,以及产生出来的声音的亮度,她都觉得特别耳熟。对,不仅仅是耳熟,那个声音上其实蒙着一层她感到陌生的东西,一种轻微的沙哑,由年龄带来的沙哑。
她很奇怪自己对这个声音的反应,忍不住也转过身,看了一眼那个正在讲电话的男人。
一个熟悉的背影,一个让她完全不敢相信会出现在此时此刻的背影。瘦高,挺拔,混在离乱汹涌的人潮里,她都可以轻而易举第一时间识别出来的一个背影。那个走路的姿势,那个步态,那个走动时手臂晃动的节奏,都是那么熟悉。
可是这完全不可能啊。她这是在市图书馆,一栋这座城市里她几乎都要遗忘了的建筑里。这个背影怎么可能会这个时候出现在这个地方呢?不对不对。肯定是她听错了,看错了。都什么年纪的女人了,怎么还可以做着电视剧里才会出现的梦。她非常果断地判定自己的失误。可是,为什么,她觉得自己的心却不受控制地,腾腾地,比往常跳得更快了。她和自己的反常对抗着,希望自己能尽快回到刚才的,正常的,安全的状态,然后更新完借书证,出门,打个车,去必胜客和婆婆、妮妮碰头。
但她越是想将自己扳回原形,她的身体就越是以不可控制的方式想要朝那个声音的方向奔去。左右两股力道拉扯着,让她完全陷入了五官失能的状态。以至于排在前面的两个人办完了证件,轮到她时,她连服务员的问话都没听清楚,“什么、什么”地连问了两遍。服务员不耐烦了,声音提高了八度:你到底要办什么事?!
算了算了,她胡乱地朝服务员挥了挥手,表示不要办了。她从队伍里折出来,正想着该朝哪个方向走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早已不自觉地循着那个声音的方向走过去了。
但她真的怕自己认错了人,一个中年女人,跟在一个以为认识的男人屁股后面走,最后却被证明是认错人了,那太尴尬了。她的理智稍微恢复了一点,脚步也跟着慢了下来。就在她犹豫的这一会儿,那个男人忽然挂了电话,转身折了回来。因为他完全没有预料到后面还跟着个人,折回来的速度比往常更快,和正好走上前的她差点撞上。
二人马上闪开一段距离。
是你?男人发现了她,有些呆住了。
就像从前的自己穿过时间的洪流来问现在的自己:是你?
如何辨认这个人还是我?她看着他,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面前这个男人又真的是他吗?身高,体型,眉眼,一模一样。又不一样。她曾经精确地掌握那个“他”的每一寸皮肤的温度,每一次笑容嘴角张开的弧度以及每一次呼唤她时声音的湿度和甜度。而眼前的这个男人,鬓角已经有些白发,眼角已经有了明显的皱纹,嘴唇也不是那样红润鲜艳唇纹清晰。
他一点点地走近她,携带着那个她曾经无比熟悉的男人身上全部的印记,但那些印记早已被时间所侵蚀。她虽然能毫不费力地辨识出他的身份,但她还是在徒劳地,竭力避免开启这个辨识的过程。
在图书馆,这座时间累积的城堡,这片岁月浮动的汪洋,光阴如无数只小兽,咻咻地在两人身边奔腾。她惊魂未定,他也猝不及防。
他们曾经经常出入于这里。骑着车,背着书包,大老远地跑来。他们喜欢这里的宁静,宁静得仿佛时间已经停止,宁静得他们以为活在了永恒里。他们喜欢这里的富足,富足的面积,书,还有无穷无尽的两个人在一起的快乐时光。她坐在一楼看书,他却总是消失,跑去四楼看古籍,看旧报纸,然后在某一个不确定的时点,又回到她一旁的空椅子上。
他们差点是要结婚的。毕业前,他得知要回老家,晚上翻过女生宿舍的铁门,跑到她住的五楼,在一屋子女生尖叫声中直接冲到她面前,问她跟不跟他走。看着他鬓角的头发胡乱地贴在还渗着汗的额角上,她忍不住笑了。他急了,拿眼睛瞪她,不准她拿这当玩笑。她当时想都没想,就点了点头。真是青涩得不可一世的年紀,以为自己的命,可以想怎么交出去就怎么交出去。
他回家了,然后是等她,以从未有过的谦卑姿态。家乡漫天翻卷的桃花,将他搅得情飞意乱。他相信他们之间伤筋动骨的爱,相信她毫不犹豫的诺言。他想像着有一天,她灼灼如桃花,以最美最轻盈的姿态飞入他的眼帘。
可她沒有来。表面上,是她没能赢过那场以爱为名义发动的、以亲情相要挟的战争:因为她是唯一的孩子,因为她是大城市的孩子。其实是她自己怯懦了,她被父母亲友所预言的现实压力给吓倒了。她完全不是自己所希望成为的那种意志坚定的人,家人的泪闸一打开,她就服软了。她连续地做恶梦,梦里向他求救,向他忏悔,祈求他的宽恕与责罚。醒来后,全身大汗淋漓。
后来她终于明白,她从来就无所谓选择,也不需要选择。规定好的命运早已用心良苦地在等着她。她始终记得,她再一次走出家门的那一天,窗外的天空苍茫一片,透着蚀骨的痛。
他们不再联系。她根本就不敢和他联系,也怕听到这个人的任何消息。
可是,人总是要接受记忆的审判的,就在这个堆满了他们的记忆的空间里,他们又遇到了。
是我。她很确定的回答。你好呀。她接着问候到。她听到自己的声音平稳,语调正常。就像任何一个正经八百的社交场所,她甚至主动伸出手去和他握。
庆幸他们终于是老道的中年人,可以瞬间装作什么情绪都不曾有过。
嗯,挺好。他也微笑着,伸出手握了一下。
她心中一沉,又马上把手收回。为了避免声音影响他人,他们一齐从出口走出来,在图书馆大门前,如同最普通不过的朋友重遇那样,寒暄了几句。原来,他是到上海开一个学术会议,顺便到图书馆来查查资料。
大概现在只剩你还在坚持做研究了。她笑了笑。同时打开手机看了一下时间,婆婆和妮妮这个点应该快出发了。
有事?他问。
是的。她有些歉意地笑。
那好吧,再联系,我在上海还会待几天。他于是送她走下图书馆前的台阶。那段他们曾经走过无数回的台阶。走到最后一梯的时候,他朝她挥手再见,就在他伸手的那一刻,她看到了他肘上一块疤痕,就在她依然清楚记得的那个位置。
她也挥手道别,扭转头。扭转头后,她再也没敢回头。她面不改色,心却碰碰、碰碰,快要从身体里跳出来一样。她还是装得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跺着步子去路口打车。在经过一家有玻璃外墙的公司门口时,她才想起来看看今天自己穿的是什么衣服,发型是否还得体。玻璃外墙照得不清晰,只看到一个苗条轻盈的身体轮廓。这让她松了一口气,她才不要从镜子里看到自己脸上那两道深陷的法令纹。她拉了拉衣服的下摆,姿态万方地等在了路口,一阵风吹过来,吹到她裸露的小腿,像有人在抚摸。
和妮妮,婆婆在必胜客吃完披萨,她又照常去了单位上班。一下午,他没有打她电话。
下午回家,又和往常一样,老公打电话说要在外面吃饭。吃完晚饭,婆婆带着妮妮,去小区里玩去了。
她的手机,也就在这个时间段里,不出意外的震动了一下。
她一回家就把手机调成了震动。是他的短信。
晚上有空吗?见个面?
她将手机抱在胸前,像抱着二十年的那个梦。
去,还是不去?

![[哈哈] [哈哈]](https://face.t.sinajs.cn/t4/appstyle/expression/ext/normal/8f/2018new_haha_org.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