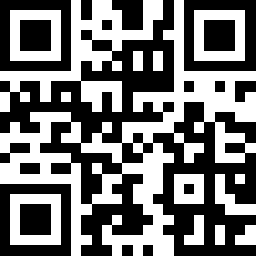军统文强:出入国共两党,从将军到战犯
文一中是文强五个儿子中,最像父亲的一个。他曾有过与父亲27年未见面的隔绝经历。
2014年7月31日,他在安徽安庆的家中,回忆起与父亲分离的那个秋天。
当时文强从长沙启程,去江苏就任国民政府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6岁的文一中嚎啕大哭,拖住文强的裤腿打滚,不愿离别。这是文一中能记起的不多有关父亲民国时的镜头之一。
在动身去徐州前夜,文强在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家晚餐,程潜提醒他“谨防当俘虏”。他不以为然。程潜是文强父亲的老朋友,1925年8月文强前往黄埔军校就读时,他已是国民政府委员。未及半年,程潜一语成谶。
1949年1月,国民党军队被困在河南永城市陈家庄时,文强接到了林彪的来信,这场军事对决快要近尾声了,国民党败象显耀。出于快速结束战斗的目的,共产党开始劝降。
仇敌原是老朋友。文强和林彪同是黄埔军校四期的同学。在1931年脱党之前,文强还曾担任过中共川东特委书记。但这层关系劝降无效,文强把信给烧掉了,他随后成为了俘虏。
文强是甲级战犯,直到1975年3月19日,才随最后一批特赦战犯出狱。受其波及,一众亲友或自杀,或被管制、判刑乃至枪毙,未失自由者也历经政治劫波。没有人能逃脱城头大王旗变幻后促狭命运的捉弄。
1、弃文从武,险断父子关系
文一中的母亲叫葛世明,她是文强的第二任妻子。两人相识在上海沦陷之后,文强任军政部前方办事处处长,负责收容从上海撤离出来的离散部队。
他们一路向内地撤离,途中遇到一个求救的女教员,因学校停办,无处安身。这个女教员即是葛世明,文强伸出了援手,这是他们姻缘之始。
“我母亲的出身、教养都比父亲好。”文一中说,葛世明是宁波人,复旦大学毕业,父亲是工商业地主,在抗战期间与她的母亲疑受日军细菌战影响,先后死于猩红热。
文强其实出身也不错。据文一中提供尚未公开出版的《劫后余生世纪履——文强将军回忆录》,他出生于湖南宁乡县文江乡,曾祖父是名副其实大地主,神主牌上有满清皇帝所赐的“光禄大夫”头衔,祖父则降格为中地主,到了他父亲一代,已是小地主。他的父亲文振之,曾东渡日本,在一所法政学校就读过一年,先后在家乡创办文氏育英小学和崇实女子职业学校,自任校长。
就与军事的关系而言,文振之与徐特立、程潜、李烈钧、章士钊等人均有交谊,且曾任蔡锷幕僚。
文强的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曾读过私塾。文强父母生有三女两男,长女早夭,幼女也未出嫁而病故。
文强是家中长子,关于他的生年,相关传记均以1907为准。据文一中介绍,文强原本一直自称生于1904,直到去世前不久才说生于1907,和黄埔四期的同学林彪同属羊。家人对此并未深究。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提及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是他的姑母,他是毛泽东的表弟。但也有人查证文氏家谱,文七妹只有三个亲哥哥,并无文强之父。文一中表示,文强生前也和他们说过与毛泽东的亲属关系,“姑母肯定是姑母,是不是亲姑母我们也没细问。”
1925年,文强在长沙就读艺群美术专科学校时加入了共青团,参加过声援“五卅惨案”运动的示威游行,也第一次接触到来自广东的《黄埔潮》等杂志,知道黄埔军校的学生正在东征南讨。这一年的8月,在入团监视人黄基永的动员下,文强一行八人去了广东。
公开出版的文强传记与口述中,均称其此行专为报考黄埔军校;查尚未公开出版的文强回忆录,他事实上去广东第一目的是报考广东大学,其次才是黄埔军校。8人中,文强是唯一均被两所学校录取者。
因距离开学还有一个半月时间,为节省开支且有收入,文强在省港罢工委员会文书部担任收发工作,住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内。居此期间,时常有黄埔学生或毕业后提升的青年军官前来聚会,他们总是针对文强想读广东大学的想法泼冷水,大批资产阶级思想。让文强一生记忆深刻的是,这些人将广州学校分为三类:黄埔军校黑而臭,是革命的;岭南大学香而艳,是反革命的;广东大学保而守,是不革命的。文强被刺激得竟彻夜失眠。
受革命气氛渲染,经过激烈思想斗争,文强才最终投身黄埔,弃文从武。他此后命运自此底定。
文强的父亲收到他考入广东大学的喜讯后,专程前来广州看他。待见面发现他“丘八”打扮后,一言不发的注视他好久好久,才斩钉截铁说:好铁不打钉,好儿不当兵。要与他断绝父子关系。文强向程潜、李烈钧求助,才缓和父子关系。
文强父亲曾做过蔡锷幕僚,仍反对儿子从军,可见当时报考军校并不为一般家庭所接受。
2、黄埔“师俄”,入党再脱党
进入黄埔军校,文强被分配到政治科受训,刚入校时编在第三团第一营第二连。据他回忆,当时政治科中几乎三分之一以上是共产党员,三分之一以上是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右派是极少数。
政治科的学习以“师俄”为中心口号。在文强记忆中,所有政治课程,几乎都是由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政治教材中精选出来。在此学习一个月之后,文强与毛泽覃(毛泽东之弟)、周恩寿(周恩来之弟)等三十余人加入了中共,周恩来是监誓人。他也经邵力子介绍,加入了国民党。
军校生涯中,值得记述的是每周一上午九时到十一时的总理纪念周仪式,全校师生(包括距离军校本部十多华里的沙河分校和五六华里的蝴蝶岗新校址学生)都要前来,集合在主席台正中悬挂的孙中山遗像前,聆听校长蒋介石、党代表汪精卫等人的演讲,口号山呼海应,“好像宗教仪式”。
在黄埔军校,文强经历了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具有双重党籍的文强,退出了国民党。毕业后,他参加了北伐,最初是誓师筹备委员会宣传组组长,后进入北伐军总政治部,任组织科社会股股长。1926年9月,他被组织抽调跟随朱德进入四川工作。
随着朱德等人的到来,万县成为了四川的一处革命灯塔,但此景不长,预感到军阀杨森可能要下毒手之后,文强等人于风雨之夜,离开了四川。
回到长沙,在文氏世馆,家乡亲友告诉他,湖南在“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下,“痞子”当道,秩序乱得难以形容,乡下有钱人纷纷向城里跑,因为相较乡下“全痞子”世界,城里还只是“半痞子”社会。文家的“赌鬼败家子”文运大当上了农会会长,人称“乱搞七爷”。
城里的轿夫大都失业了,因为乡下农民自卫队和儿童团一见轿子就打,见穿长衫的都剪成短袄,见妇女留长发也要剪成“瓢鸡婆”(短发)。文强好不容易找到两名轿夫,见其是带着三角巾的革命军人,才答应前往乡下。
文强回到距离长沙三十公里的家乡,亲眼看到被发动起来的数百贫农男女,时常冲进大户人家,轻则批斗,重则绳捆索绑戴高帽游街,且要杀猪宰羊大吃大喝,开仓“济贫”。“一连数月,没完没了的干,养活了一批流氓地痞,使无业流民越来越多,既扰乱了社会秩序,也破坏了生产。我乡向来民风淳朴,人民生活也颇为恬静,自农运兴起,盗贼也多了起来,务正业的农民都敢怒不敢言。”
1927年5月21日,“马日事变”爆发,北伐军中的35军33团团长许克祥针对湖南省总工会和农民自卫军展开军事行动,并释放在押“土豪劣绅”。此时文强刚从家乡回到长沙,混乱中逃离出湖南。
虽然在晚年回忆时,对湖南农民运动颇多检讨,但从文强当时的表现看,他仍站在激进革命的这一边。八一南昌起义文强也卷入其中,兵败后逃至香港。1928年他再度赴川,继续从事农运和共产革命工作,经过几年打拼,升职为中共川东特委书记,领导川东23个县的地下工作。
1931年一次被捕的经历,改变了文强的人生轨迹。按他个人说法,他在内应的帮助下逃狱成功,但中共四川省委临时书记罗世文以其被捕后供出打游击情况为由,给予“留党察看”处分。文强辩称,自己暴露的只是敌人已知的信息,在此基础上以假供词迷惑敌人。这个说法不被罗世文接受。
考虑到很多被清洗的中共党员彼时都被“装在麻布袋里扔到嘉陵江里去了”,三思之后,文强与妻子周敦琬决定离川,回长沙老家。周敦琬比文强大三岁,毕业于燕京大学,父亲曾留学日本修习法律是一个法学家,姨夫也曾在蔡锷部下就职(任参军)。周敦琬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妇女部长。这次出走后,周敦琬脱离了政界。
3、厕身军统,卷入内战,
在长沙,文强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任少年通讯社社长。按照文强个人说法,他和周敦琬曾多次给上海党中央写信,但石沉大海。
在脱离共党五年之后,文强重新加入了国民党。
1935年底,因少年通讯社刊发的社论惹恼当局,故文强避走他乡,来到了杭州。他黄埔四期的同学廖宗泽此时名义上是南京军事杂志社记者,但真实身份为浙江省警官学校甲训班队长。廖宗泽邀请文强出任警校政治教官。
浙江省警校受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特派员戴笠监督,戴笠是黄埔六期生,但年龄比文强大约十岁。与戴笠的结识,促成了文强一生中最广为人知的职务:军统特务。
到浙江省警官学校任教后,程潜写了一封信让文强交给张治中(曾任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长),张治中找了五个黄埔学生,联名证明文强已脱党多年。他重新加入了国民党。
在文强的前半生中,黄埔军校的经历至关重要,几乎每一次职业生涯的变动,都离不开黄埔师友的引荐与提携。
文强在军统崛升很快。抗战爆发后,他出任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后转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统一委员会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代表军统局驻在上海,负责对东南五省汉奸政权进行策反。1941年,他成为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长、少将政治部主任。此时正是国共合作期间,按文强说法,他并未和共产党产生冲突。
在抗战爆发后5年,他一直在上海租界内从事特务工作,直到1942年回到重庆后方。
1942正是文一中出生那一年,蒋介石在重庆接见了文强,指派他去太行山敌后根据地,监控孙殿英、庞炳勋部,配合胡宗南主力部队,抵制日寇和八路军——此时国共的摩擦已愈演愈烈,皖南事变发生在一年前。
文强的妻子周敦琬已在1941年去世。她患有子宫瘤,动手术时,日机前来轰炸,医生慌乱中将手术刀遗落在其腹中,不久后她就去世了。文强和周敦琬生有一子,文致中。
对孙殿英、庞炳勋的监控难称成功,他们相继投靠了日伪。不过此时,受太平洋战争的牵制,日军已是强弩之末。1945年抗战胜利,文强出任军统东北办事处处长等职,东北正是国共双方角力重要区域,文强自此陷身内战,成为东三省反共活跃人物。
1946年,文强晋升中将。
而一路蹿升的文强,终究无法背离国民党的衰落大气候。1948年参加淮海战役,邀请他出任徐州“剿总”副参谋长的杜聿明,同样是他的黄埔袍泽。
“大雪未止,天候更寒。定投绝望,闻各军第一线士兵为饿寒所迫,竟有少数逃入敌阵者。若再连续三五日降雪,而定投不能接济,则三军祸生肘腋,非战之罪,乃天亡我军矣。”
这是1948年12月24日,文强所写日记的开头部分。结尾处,他补录了23日夜所做的一首七言律诗:
连年烽火月中霜,云树低迷古战场。
北上援师断归路,西征劲旅渡关乡。
漫漫白云张天幕,冷冷军旗蔽日光。
倦依战壕筹善策,豪情举酒烹牛羊。
其实,连日下雪,日光岂需军旗来蔽?几近于绝路的包围圈中,饮食几乎全依不靠谱的空投,哪有酒和牛羊,又哪有豪情?在这首强说豪情的新词之后,文强中断了日记,16天后他成为了解放军俘虏。
除了被俘期间,文强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也喜爱写诗。文一中说,被俘的国军将领黄维对文强的评价是“书呆子,胆子不大”。
4、接受改造,亲友受株连
文强被关在北京战犯管理处,1958年转到秦城农场。他和很多黄埔校友在那里接受新政权的改造。
第一批战犯的特赦是在1959年,北京仅杜聿明等十人恢复自由。文强在文革即将结束的1975年才走出秦城的高墙。他在1983年出版的《新生之路》中写道:“有次一位军管干部悄悄的对我说:‘你们是坐在保险柜里,不必担心。因为你们是历史罪犯,是‘名牌’,不同于党内‘走资派’,他们是暗藏的。”
文强在狱中平安度过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等政治高压期,但他亲友却没有这么好运,受株连者甚多。据《文强口述自传》,他的亲弟弟、弟媳妇,在土改时被殴打,抱着石头沉水自尽。大伯父因受文强引荐在唐生智手下做过译电室主任,也受到牵连,后饿死。另一位在文强帮助下成为国民党上校的二叔父,则被枪毙。文强任长沙公署程潜办公室主任时,任用的几个同乡,以及当地敬信学校一位文姓教员,因土改时家中搜出文强照片,也被枪毙。
“不仅是这些人,就连我父亲的勤务兵,都被判了十五年。他一个勤务兵,其实对相关决策啥都不知道。”文一中说。
在文强被俘时,文一中已随母亲葛世明去了台湾。葛世明一个人先坐飞机回到大陆,而后发电报叫她的乳娘带文一中兄弟三人回来,“她总认为,仗打完,应该放人了。”
文一中是坐着台湾到上海的最后一班船回来的,听说外婆为买到船票花了几根金条,临下船时,随身携带的细软被副官一卷而空。
据文一中介绍,葛世明初回大陆时,去山东关押文强的大院求见,未被允许。她每日哭,钱花费殆尽,连首饰都卖光了,又回到上海,总是生病,有脑膜炎,还受刺激得了精神疾病,后来信仰基督教,精神状态有所好转,在立信会计学校教书。
但接下来的政治审查,葛世明终于没有熬过,1955年春,她打开家里的煤气自杀了。
文强的五个儿子中,二子早逝,长子文致中参加了军人干校和抗美援朝,在湖南土改中也表现积极,后在一家县报工作,妻子是当地妇女主任。虽然努力与新政权靠拢,但他后来还是被打成右派,宣布与文强断绝父子关系,文革后父子关系修好。文致中晚年曾任湖南南县政协副主席。
三子文一中在安徽华阳河农场任技术工人至退休。据他介绍,1959年曾因讲了一句“反动言论”:“你们不知道哎,饿死了很多人”,而被劳教两年。
四子文贯中,现为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在大陆多家媒体开有专栏。五子文定中,在北京开有一家饭店。
自1948年别离后,文一中再次见到父亲是在1975年4月。文强出狱后来到上海,除文致中外,几个儿子都到了那里。“第一次见面,我们都叫他‘父亲’,不叫‘爸’,一直如此,不知道为什么。”那种距离感,一直保持到2001年文强去世。
文强出狱后,被分配到全国政协担任文史专员,1983年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次年,全国黄埔同学会成立,文强出任理事,同时担任北京黄埔同学会第一副会长,为统战工作尽了心力。
文强时常会给儿子们讲述过去的故事,对国共领袖也多有臧否。有时候,他的孩子们也会议论一下国是,“说话如果狠了一点,父亲就会说:这话不能这样讲,在外面这样讲是要杀头的。”
当年在敌阵营出生入死从事特务工作的文强,经过20余年的改造,胆子的确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