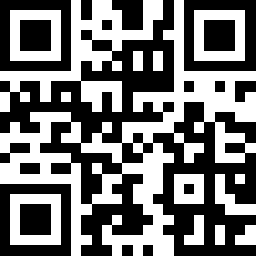为了12米的杂志墙
2015年11月22日 20:09
阅读 7818

12米的杂志墙
令狐磊
12米,
对于正常人来说,15秒就能走完。它不长。
但如果它是一堵琳琅满目,收藏着来自全球的优秀的杂志书墙,我足足走了15年。
我是一个杂志人。但这个职业无法写进中国的七十二行里。一席之前做了38场演讲会,300多位嘉宾,我看到里面都是各行各业很有意思,很能代表现在中国创造力的人物,我演讲口才有点笨拙,还有镜头恐惧症,本来想拒绝的,但当我听说还没有一个人好好讲过杂志。我觉得这对“杂志”这个文化产品来说有点不公平。于是我来了。
让我们把眼光看远一点,一千年前的宋朝,我们都知道的大文人苏东坡。他的身份,除了是一个大文豪外,他还是旅行家、大书法家、画家、造酒试验家、瑜伽修行者、炼丹术师、建筑园林家、城市规划师。如果他活在今天,我想,他还会办一本杂志。天纵之才,总要有一本本杂志封面来帮他抒发。
杂志人是些什么人?他们是知识分子,又不完全是;他们是媒体人,又不完全是;他们是生活家,又不完全是;他们是创意人,又不完全是。
为了把他们从文化人、出版人、媒体人里区分出来,我觉得可以创造一个词“Magaziner”,杂志人这个词一直存在于中文语境中,但从来没有一个明晰的定义,在当代中国,这个行业的从业者甚至没有超过20年。
放眼到全球,即便是西方世界,也没有明晰的范畴来定义他们,正如我们所认为这些杂志人,也常常处在媒体人、艺术家、设计师、企业家、作家、电台主持人这样的社会角色的夹缝中,呈现出混合、交错和复杂的面容。
于是,我们可以把办过杂志的Andy Warhol视作是杂志人的一分子,我们也可以把经常绘画杂志封面的达利看作是杂志人的一份子,但似乎从来没有人把这些人拉入这个领域。
我们至少知道,杂志总是属于天赋之才的。或者是属于懂得欣赏、向往这些才华的人的读物。
我在新浪微博上有一个账户,叫“令狐磊的杂志发现室”,从2009年的10月开始,我就开始帖我所发现的有意思的杂志和相关消息。我认为,杂志的封面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它是资讯、虚荣、权力感、设计、美学和主编态度的高度浓缩的产物。
以下是那些最受欢迎,最多人转发和关注度很高的杂志封面。
以下是我觉得很值得向大家推荐的最灵的杂志。
这本是我做了很多年的杂志。我参与了它的创刊,和无数个风雨日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把封面交给艺术家,让艺术家来创作封面。
一共做了十年,我参与了近120期。做杂志便是这样的工作,它很杂碎,但看上去又只做了一件事情。“你是做什么的?”“做杂志的。”“哦,那你们是月刊还是双月刊,你们印多少本。”这些简单的社交场合的闲聊每每到此为止,没有人会问你上一期以及下一期杂志做了些什么。
这个工作很平淡,但它绝对是需要很高的注意力和意志力才能去做的事情。每一期都要倾尽所有心力去完成,才能有所表现。如果一本杂志不是你自己办的,在合适的时候懂得交给更年轻、更有才华的人来做,这对于这本杂志是件好事。
这是我离开我的岗位的时候,我收拾了一下桌面,拍摄的一张照片。
我似乎要对自己说,我需要新的开始。
很多人这个时候就会说,你去做网站?做APP?做新媒体?
做这些当然都蛮好的。但我的个人经历告诉我自己,全员加入数字媒体会是一场灾难。我在1999年到2001年,在第一轮网络泡沫之前便是一个网络公司的兼职编辑,在那些周而复始的更新中挥霍青春。人有很多价值呈现的空间,也有很多需要文化人去发挥才智的地方,不需要太多的趋同性。我当年选择去做杂志,而不是新闻系同学一般考虑的报纸、电视,就是想做不一样的我。
我们现在的地铁里已经是这个境况,从上海到东京到巴黎,只要地铁里有信号,每个人都会掏出手机。但我们从以前的《纽约客》封面上看到的纸媒年代的地铁里,是这样的丰富充满多元的想象力。我在想是不是要问一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丢失了什么?
这是1940年代的报摊,我们可以看得见《时代周刊》《LIFE》画报,那时的中国,还是动荡不安的时代,但人们能看得见世界。
这张是1947年的报摊,玛格南的摄影师拍摄,我们同样可以看得见国际刊物,也能看到中国人办的科学画报、观察杂志、电影杂志、音乐杂志、文学的论语、旅行杂志、少女杂志。
没有事情的时候,我喜欢看报摊,更喜欢到书店里呆着。有一天,我到里斯本一个叫Ler Devagar(慢阅读)的书店,它有十多米高的书墙,中间悬吊着这个装置作品,一个骑单车的少女,围巾迎风而飘,自行车被艺术家加上了翅膀,借助电力驱动,它就在上空扇动着翅膀,飞啊飞啊,我看着看着就看呆了。
我们这些飘在空中的文化旅人,何时会是我们的落脚点?
这里便是我的新的落脚地。我们不只是需要一本本书,一本本杂志,我们需要文化场所。只有场所,能让我们从屏幕的控制中走出来。
衡山路,我们考察了衡山路,它旧称“贝当路”,是原来法租界的优雅梧桐树大道,人们从中心区通过这里直达徐家汇大教堂、天文台,当年的租界里最好的花园洋房都在周边,这里的小红楼是当年的百代唱片公司,周璇应该在这里录制过金嗓子的歌声,费穆、赵丹等著名电影人都住在这一带;解放后1950年这里经市民自发筹集盖了新中国第一座的市民电影院。因为环境雅致,在1990年代,重新对国际开放的上海,衡山路成为第一代的酒吧一条街。直至近些年“街”道中落。它需要重新的定位和复兴,正如我们凋零的城市文化生活一样。
我们定义的衡山和集是一次新的实验,我们探索在都市里那些需要重新复活的老建筑里,能不能做特别时髦的、摩登的事情:比如开一间集合店,有书、杂志、艺术展和时装以及很多好玩的东西。我们可以做一个文化的客厅。我们也可可以更简单地做些牛逼的事情,比如是做一个12米的杂志墙。
2014年的秋天,例外、方所的创办人毛继鸿先生在上海衡山坊发布其新一季的时装,这场秀是让模特穿梭于梧桐树下的小洋楼之间。走秀结束后,他指着其中一栋楼说,我们要做一个属于杂志的博物馆。这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事情,即便对于当时我还是一个杂志的从业员的角度来看,拿出一整栋商业空间来做杂志的陈列、销售,这都是一件疯狂的事情,有点向杂志业致敬的意思。我问毛总为何要这样做,他说:“杂志对于他这一代创作人、设计师来说,是一把打开世界的钥匙。”
其实,我们大约在3年前,方所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关于建一个杂志博物馆的讨论,当时做还是觉得需要很多的资金和空间,没想到老毛还记得这个事情。于是我就决定开始要加入做这个事情,可能一开始我们做的还不是真正我们理想的那样,我们可以从这个开始。
好了,这是当时的落柜图,商业开发部门要求我来做一个落柜说明,这对我是一次挑战,因为我这个杂志人,只懂得做排位表。但很快我发现,把内容放到格子里和放到实体空间的格子里,两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这个墙欢迎所有爱杂志的人都来看看,一起交流哪本杂志这期做得好,哪本这期不是那么好。在很长的时间段内,中国杂志人并没有太多一览众山小的机会,不能像东京杂志人、巴黎杂志人和伦敦杂志人那样,有一间可以让他们迅速了解杂志世界当下的较为全面的动态的杂志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像在闭门造车一样,自己做自己的,或者看旁边的广告卖得好的我们就跟着做,我们并没有太多的全球视野。这也是我这一代杂志人的悲哀,我希望未来一代的杂志人、创作人肯定眼光会比我们好。
所以尽管我现在不再专注于《生活》杂志了,也不代表我对杂志业灰心了。相反,我是要以这12米长的墙,去鼓励大家,还有那么多的好杂志在坚持着,我们还没做出属于我们的杂志黄金时代,怎么能放弃。
在1998年的时候,我做了一本以我自己为号的个人杂志,现在来看可以归纳为“自媒体”;作为一个新闻毕业生,我没有进入报业或是电视业,而选择了杂志,也是想做一个不一样的我;我从《新周刊》到《生活》月刊,是为了体验快与慢、反对与建设之间的多元价值;之前我做杂志发现室,如今去策划一个杂志博物馆。为什么我依然在执迷于做杂志这件事情?
我是觉得,杂志本身是对生活方式的投射。我们太多时候把杂志看作是一种产业,但它对于读者来说,只是一种生活。杂志的品类、品质也完全地取决于我们生活的丰富度和厚度。我们如果做不好杂志,不是因为我们没钱,而只能说我们过不好自己的日子。
(本文为一席演讲备稿,现场并不完全按照此稿发言)
正在加载中,请稍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