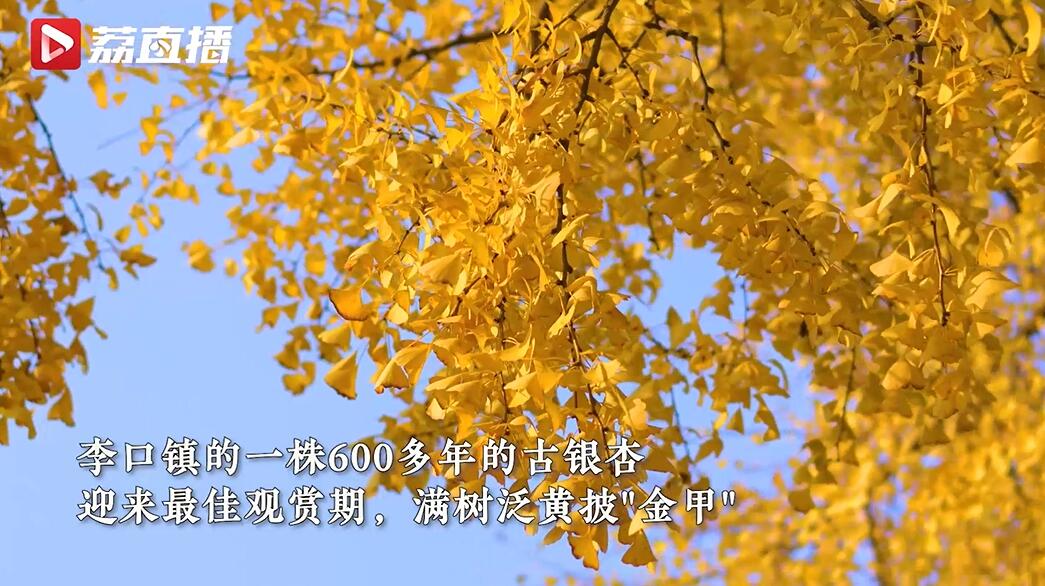陈颙院士 吴宇 摄
陈颙,教授,博士生导师。196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物理系。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8年获得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2000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地震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主任;现任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长。从事地震学、岩石物理学和高温高压下岩石物理实验研究,揭示了应力途径对岩石的性质的影响,发展了测量岩石变形的激光全息技术,发现的岩石热开裂现象被广泛应用于核电站的安全性监测。致力于地震预测和地震灾害研究,将地震学、工程科学和经济学结合在一起,编制的全球地震图和全球地震灾害预测图,已被联合国等机构用于减灾计划。
一盏灯,可以照亮一方。有一个人,却想在中国的土地上,点亮可以探寻地底奥秘的明灯,实现“天上有北斗,地下有明灯”的梦想。
与陈颙院士相约在一个早晨,阳光不燥,微风正好。一行人穿过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办公楼长长的走廊,廊内的玻璃展示台里黑黝黝的化石,悄无声息地向路人传递出许多信息;墙面上贴着的学生、老师去各地调研、采风的照片,让人感受到了从事地球科学研究的科研人员的乐观、豁达。
“1942年出生的陈颙,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8年获得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2000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一路上,我们默念着陈颙院士的简介,已来到了他的办公室前。
阳光透过窗户,洒进办公室,书橱里、书桌上堆放着一摞摞书籍和资料,“不好意思,有些乱,没来得及整理。”生怕桌上的书籍挡住交流的视线,陈颙院士招呼我们坐下后,起身和助理一同收拾了起来。
一张桌子,两盏热茶,开始倾听陈颙院士的故事。

陈颙院士 吴宇 摄
父亲的科学启蒙
陈颙院士的名字很特别,在采访前,很多朋友说,经常看到陈颙院士的名字,可是这个字却不认识。
陈颙院士笑了笑,用带着些北京口音的普通话告诉我们,父母在他出生的时候,向当时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的一位老先生求了“陈颙”这个名字。至于,“颙(yóng)”是什么意思,后来,陈颙自己查阅了《辞源》,才知道“颙”的解释:一曰“大”,二曰“仰慕”。作为家中长子,他渐渐明白了老先生的良苦用心和父母的期望。
在陈颙看来,他的科学素养离不开年轻时打下的良好基础。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许多终生难忘的好老师、好朋友唤起了陈颙对科学的兴趣,并使这种兴趣一直保持了下来。
8岁那年,陈颙全家迁居北京,他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小和附中完成了学业。说起上小学的经历,陈颙仿佛回到儿时,带着股骄傲劲儿说:“我的学校是我自己找的。”原来,陈颙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单枪匹马跑到小学顺利通过入学“考试”,被正式录取。几年后,他作为优秀生顺利升入中学。
在陈颙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做事极为认真的人。作为一名数学教师,父亲坚持每次上课前,一丝不苟地写出教学纲要,针对不同年级、不同学生的特点制定出相应的教学重点。父亲对陈颙的启蒙,也有自己独到的坚持。
中学时每逢周末回家,父亲总是笑眯眯地拿出一页划了几行字的纸,对陈颙说,这里有两道数学题,我解不出,你拿去看看吧。这时,陈颙总是欣然领命,默默地走到另一间屋子里,关上房门,静静地思索。当陈颙走出房门交出答卷时,他总能隐隐地觉察到父亲慈爱的眼光里露着一种满意。若干年后,陈颙才知晓这些题目都出自历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试题。陈颙回忆,自己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尤其是年少时对数学的热爱以及扎实的数理基础,大都得益于父亲那随意却又独特的教育。

学习就要“走心”
陈颙院士时尚,又让人容易亲近。走路间隙的闲聊,老先生从淘宝购物聊到圣诞节打折促销。西装裤配上户外鞋,活力十足。“你看我这鞋子,就是打折抢购的,只要10美金。”陈颙院士擅长“学习”,聊起如何“学习”,陈颙院士用了一个流行词——走心。
讲到学习,陈颙院士说,“我有个小故事和你们分享。”
陈颙院士记得中学时每周都有一次考试。初二的一次物理考试,题目只有一道:“从行走的汽车上横向抛出一只皮球,问站在路面上的人看到这个球的运动轨迹是什么?”分数出来后,陈颙破天荒拿了个不及格,这是他学生生涯中的第一次不及格,也是最后一次不及格。从那以后,陈颙的学习态度变得端正起来,成了一个爱动脑筋、爱动手、努力学习的孩子。
1957年,陈颙顺利升入高中。因为历史原因,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陈颙却在这段时间里自学了高中三年的数学和物理课程。尽管对内容的理解与掌握较为浅显,但主要概念与方法都深深地印在了陈颙的脑中,这对他今后的学习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高中三年级时,陈颙因为成绩出色被选为老师的任课助手,他常常利用业余时间为同学们答疑。那时,让陈颙最兴奋的莫过于摸索出“一题多解”后的喜悦。陈颙笑称,他对知识的掌握非常“走心”,毕业33年后,有位同事拿来1990年的高考数学和物理试题,他都能不费力地解答出来。陈颙感叹:“若非当初主动学习知识,只是机械地死记硬背,恐怕再也没有这份从容与自信了。”
庄子曾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面对无穷无尽的知识,陈颙很早就明白,对知识的精确掌握固然重要,但更重要是要明了如何学习,总结出一套适合自己特点的学习方法。
陈颙院士也将他的学习方法分享给大家,概括起来有两句话:学习靠自己,自我为主,老师为辅;学习要有动力和浓厚的兴趣。

与地震科学结缘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发生了多次六七级地震,不少还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大、中城市。地震最频繁最危险的时候,也是陈颙最忙碌的时候。1965年,陈颙大学毕业,此后他一直从事地震学和实验岩石物理学研究工作。
“这其中,故事太多啦!”也许是看过太多的地震现场,回忆中,陈颙院士的语气苍凉中有着些许平静。1966年,河北邢台发生强烈地震后,陈颙受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派遣,前往震中区进行现场工作。“当时,坐在车上,头顶着一片灰蒙蒙的天,我们来到破坏最为严重的震中现场。没有人说话,死一样的沉寂笼罩着每个人,我的心被一种震撼冲击着。”
“当时,就想着,我们必须做点什么。”陈颙院士说。
什么样的地球物理观测对于地震预报研究最为有效?早在1887年,我国就有了近代最早的地震仪器记录(并不比国外的地震记录晚很多);1930年,李善邦先生在北京鹫峰建立了中国人第一个震台站,但是,中国学者正式重视地震问题的研究始于几次惨痛的代价之后。
陈颙告诉记者,大学时,所有的知识都只是纸上谈兵,与真实的现场完全不同,震后的满目疮痍让他久久难忘。这一段工作经历也让他记忆深刻。
“当时,各种地震仪器被震坏了,就小心地从里到外检查一番,然后再拆拆补补,卸卸装装。”对陈颙来说,那时,最开心的时刻莫过于让一台仪器起死回生,看着它在地震现场大显身手。现场资料的处理和结果的分析大都在结束了一天的测量之后进行,窝在小小的野外帐篷里,陈颙沉浸在铅笔与计算尺的交替运算中。
“你们想象不到有多辛苦,既要警惕余震,还要忍受没有交流的寂寞。”因为检测设备设在野外,十天半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最多只有两个人在一起工作,若是有同伴请假,就只能一个人盯着地震图和各种仪器……寂静荒野,此情此景颇有一番苍凉之感。

一诺已行数十载
在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大楼的墙壁上,挂着一副巨型地图,上面有五颜六色的色块标注。常经过这里的学生和老师能看到这样一幕场景——图下,陈颙院士正专注地对着地图思索着什么。陈颙院士在结束采访送我们离开时,又习惯性地在这里停留了一刻,指着图说:“你们看,这些有颜色的,是我们已经了解到的地质情况,但是还有太多地方我们没有了解。”
已经70多岁的陈颙院士,从未停下他探索的脚步。“我现在也遇到一些困惑。”陈颙院士明朗地笑着说:“就是身体状况确实没有以前好了,但思维却越来越活跃。”从1965年,陈颙院士到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参加工作至今,已经过去了50多年,是什么让他在自己的岗位上孜孜以求?陈颙院士说:“我有一个座右铭,特别简单,叫做‘做好小事’。”
在陈颙刚工作的那个年代,地震领域研究还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在地震这种毁灭性灾害面前,人类显得非常渺小。“真的见到了那种无助与慌乱,内心不可能没有触动。我觉得,总得做点什么,哪怕是一件微小的事情。”从那时起,陈颙就决定将他的毕生精力都投入地震领域的研究中。
“20多年前,我做了一个梦。我们脚底下踩的是地球,唯一能穿透地球的是地震波,让地震波来给地球做个B超,从地球内部带来信息,告诉我们地球的变化,这样不仅可以预测地震,也能找到矿藏等,让这个梦成为现实一直是我追求的目标。”
陈颙院士说,在寻找区域性人工源的过程中,他的团队经历过多次失败。“科研,哪是那么容易成功的呢?我们最早用过炸药,可是危害很大,后来也用过火车震动的声波、汽车震动产生地震波等,都失败了。后来,开展了以有限水体作为人工震源的深入研究工作,终于取得了成功。”
有限水体只要配合发泡气枪,就变成了一个新型绿色人工震源发射台,震波覆盖面积近500万平方千米。这就意味着,只需在全国建设10个容积5万立方米的有限水体,就可以组建成震波覆盖全国的人工震源发射网,形成探测近地表的“地下明灯”。如今,这样的“灯”已经亮了四盏,陈颙院士说,“希望,我能完成这项事业。”
(来源/江苏科技报;编辑/黄河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