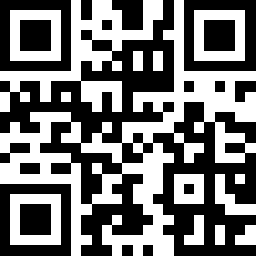关于东北那点事儿(十七)
昨晚有个博友问我从齐齐哈尔到内蒙的满洲里开车要多久,我说我们开车大概四五个小时,外地驾驶员要六七个小时。中途还有一段沉降路,而且过隧道的时候一定要减速进入,为隧道里边有冰。他回复的话果然没出乎我意料:现在就结冰了?索性今天有空,因就讲讲东北的冰与雪吧。
我记忆中小时候的雪是非常非常大的,以至于这种记忆一直保留到前两三年。那时候气候也远比现在冷很多。小时候我们冬天基本就没穿过正常尺码的鞋。秋天的时候,每家每户的主妇们就要做棉鞋了。把一块一块的碎布黏合起来,叠成厚厚的带着浆糊的布片,我们这叫:打疙呗。大概就是这个读音吧,具体这词咋来的也不太清楚。然后就裁剪出来纳鞋底。锥子,顶针,麻线或者搓成的白线,一针一针的把布片缝合成厚厚的鞋底。然后再把趟绒鞋面絮上棉花缝上。这双鞋比孩子的脚要大一些,因为里边还要穿一双毡袜。我小时候是很怕穿新鞋的,因为鞋底很硬鞋帮开始也会磨脚。这双鞋象铁板一样又厚又硬不跟脚。
那时候平房的窗户外边大多都有棉窗帘。晚上睡觉前要把外边的窗帘挡上,然后用绳子系住或者用砖头压住,这样才能保证室内的温度不会流失的太快。当晚上睡梦中听见窗帘不断的敲击窗子,不用问又刮风了。那时候的风真的象刀子一样。第二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出去把窗帘卷起来。不过刮过风以后通常是第二天早上打不开门。得用力的用肩膀去撞,慢慢的撞开一条缝,然后就看见半扇门那么高的雪,接下来的就是耐心活了,拿起炉边的小火铲,一点一点的把门外的雪掏进屋里然后再把门撞开更大然后再掏再撞。等人能够侧身出去的时候,大人就要从雪上爬出去,用铁锹从门口到路上清出一条人能通行的路来,这活可真是个力气活,雪看起来好像很轻,但是一米厚的雪却又很重,没有一个小时的不间断的劳动是不行的。 等路通开就容易多了,因为雪在房门口收到阻挡所以才会堆积那么后,在宽敞的路上会少很多。
背上书包,去邻居家把一起上学的同学叫出来,路上会有越来越多的孩子汇集在一起,这在雪天很重要,因为会有一些沟渠被雪埋起来,一旦掉下去小孩子可能就会爬不上来。八三年四二九大风雪那天我就是一个人去上学,结果掉进一个树坑里,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才搭雪梯爬上来,而当时基本就快要冻僵了。那时候平时上学要走二十几分钟,雪天就至少要走一个小时。每走一步雪都会没到大腿根,就连我这打小就具备的大长腿也不例外。而每一次提起脚都需要很大的力气,用不了多远,棉鞋里就已经灌满了雪,这时候不要去管它,因为你掏干净了马上还会灌进来更冷的雪。就让雪在鞋里变成雪冰,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我这个年纪的东北孩子大多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到了学校,家近先到的同学早就生好了炉子,长长的炉筒子上铺满了湿湿的鞋垫还冒着蒸汽。远看还以为是哪个食品厂在烤长白糕呢。
到了学校其实也只有半天课,因为接下来还要清理操场的积雪,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分担区,男孩子是主力,女孩子基本就是啦啦队。能用的工具全都利用上,把操场上的雪堆成几个大雪堆,然后在老师的带领下大家把这个雪堆铲成一个雪人。鼻子眼睛嘴都有,我有一次创造性的同时也是纪实性的在雪人的肚子下边插上了一根棍子,结果人家都回教室了,我对着雪人站了一节课。等老师和同学下课后来围观我的时候,发现那根棍子旁边又多了两个蛋蛋。
那时候衣服也特别的厚,很常见的是棉猴。用现在的标准看就是棉帽衫。不过穿起来可没什么美感,离远看像个熊瞎子过来了一样。还有一种专门给很小的孩子专用的抱猴。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的班主任就给孩子用的那个东西,象一个大棉口袋,下边是封口的,前边是一道长拉链,上边是一个帽子。把孩子装在里边就好像一个不倒翁一样。那时候冬天老师每天要骑自行车驼着孩子来,进了楼里先把孩子往教室讲台上一蹲,然后老师去办公室把棉衣手套围脖之类的放下再返回教室,抱起不倒翁去学校的托儿所。而就这短短的几分钟内,老师家的家庭结构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老师前脚刚离开教室,后脚前排的男同学就凑过去了:喂,小孩儿,你叫我啥?叔叔?不对,要叫爸爸。快点叫给你糖吃。然后那不倒翁就甜甜的叫了一声爸爸。然后更多的同学都去尝试。等老师回来时,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有了十几个小老公了。
在这里要声明一下,绝非是我们班级的同学不尊师重教,我们对其他很多老师都很尊重甚至爱戴,但是对那个班主任则是深恶痛绝。要说这个老师专业其实很厉害的,因为当时我们学校是重点学校,她俄语和英语都非常好。但是她的人品确实和老师不相符了。她接任班主任后就让我们填表,把家长的工作单位职务都写上,然后就不断的对学生和家长提出一些要求,比如买个当时很紧俏的进口彩电了,让学生家长给弄点胎盘了。不过也不是总能得逞,我有一个同学那简直是赵本山的师傅,他父母都是园林处的,老师就总惦记从公园的花房弄点花,我这同学一拍胸脯说:老师你放心吧,我一定让我爸给你选点最好最贵的花儿,他们刚培育的黑月季老师你见过没有?老师一听脸上褶子都乐开了,结果一直到毕业她也没见到这黑月季,还被我这同学骗去了一个区三好学生加了二十分。
这老师还有一个地方让我们讨厌,她有一只义眼。然后这两只眼睛角度就不同。后来我们测算出她斜视角度为四十五度。但是起初不知道啊,她面对我们的时候我们还装的象人一样,等她斜过身子的时候我们以为她看不见了就开始搞小动作,哪知道人家那才是正眼瞧我们呢。走过来大皮靴子就是一通踢,而且专踢迎面骨和膝盖。而我就是挨踢的第一方阵。
因为清雪我还挨了一顿揍。那年冬天我们学校门口学生和社会青年打群架打死了一个人,过了两天下雪,然后我们就在操场清雪,这时候学校的保干就走到我跟前让我跟他走一趟,我说干啥呀我清雪呢?他说我就瞅你清雪来气你到保卫科去。揪着我就进了保卫科,然后就和我动手动脚,我当然也没惯着他,俩人就在保卫科打了起来,最终还是没打过他,妈的把我打得象猪头一样给踹出来了。老师去问他为什么打我他说怀疑我和打群架的社会青年有勾结。老师也没有什么办法,可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过了没几天,也算是老天开眼啊,这个保干在下班的时候被七八个力气特别大的好像是建筑工人模样的人用麻袋从后边给套了,枪也给下了,连人带枪给扔到学校门口的公共厕所里去了,不过没啥事,里边都结冰了,他只不过闻了点味而已。
有雪自然也会有冰。冰和雪不同,雪给人带来的是烦恼,而冰则给小孩子带来无穷的欢乐。当时街道两侧都有结冰,我们叫:哧溜滑儿或者出溜滑儿。每次远远的看到路边的冰,都要兴高采烈的来一个助跑,然后哧溜一下在上边滑出老远。小时候冬天的运动也大都与冰相关,冰车,单梯。不过我始终学不会单梯,可能因为我腿太长蹲下以后掌握不好平衡感?看着人家把单梯滑的飞快我只能望腿兴叹了。
上学以后学校要浇冰场,可是浇一块冰场需要很长时间和很多的水,所以学校就给每个学生下达了一个命令:自己在家用脸盆冻一坨冰交给学校。然后学校组织学生把这些脸盆形状的冰摆满操场,然后再浇水,这样果然一夜之间一个冰场就浇成了。然后就到了炫富和炫技的时候了。那时候一副冰刀很贵,贵到什么程度?两个家长一个月的工资。而我父母当时从冰刀厂弄出来的一副出口球刀,价格是惊人的上千块。所以有冰鞋的孩子无疑是很牛逼的。可是最牛逼的永远是那些打小就进入体校或者业余队训练的孩子。一身标准的行头,加上标准的东西,标准的鄙视我们的嘴脸,简直气死人了。不过就是这些孩子,在十几年后成为了中国速滑队花样队冰球队的主力。很多人成了冠军,也有很多人伤病退役,甚至还有的留下了终身的残疾。有个朋友是冰球队的队长,比赛中被击伤头部,当时的伍绍祖调直升机送去抢救,人是活了,不过有些地方不太对头,想说的话和说出来的话根本没联系,曾经是一个那么强壮叱咤风云的运动员,变成了那个样子,看的让人好生难过。
不过冰球队也有好笑的段子,过去这么多年了,估计这事儿说出来也没啥问题了。冰球运动员体格好,估计性欲也较强,那时候我们这里的大学有俄罗斯的留学生,反正有一两个俄妹和身体强壮又多金冰球队员混在了一起。后来发展到逃课集体淫乱,终于把校方惹怒了报了警。那时候还有流氓罪的,结果一大串队员都给抓进去了。偏巧这个节骨眼国家队集训,这下子可麻烦大了,总不能跟国家体委说队员都变流氓了吧?最后所有的部门都惊动了才算把这事儿压下去,从拘留所里出来直接去集训估计是那批队员终生难忘的事儿了。
大多数人都知道哈尔滨的冰灯。那是黑龙江的一张名片。过多的介绍我就免了,因为网上可以搜索到很多相关的信息,个人认为是很值得一看的。但是之前其实很多城市都有自己的冰灯游园会或者游览会。齐齐哈尔当年就搞过很大规模的冰灯游园会,我小时候最大一次规模的冰灯甚至踩死了人。还有一年的冰灯最有创意,一个是冰廊,晶莹剔透的冰块中放置了很多种东北人很少见的鱼类。反正我们是趴在冰上看个不停,然后自作聪明的给这种鱼取一个名字。然后最好玩的还要数那年的冰滑梯。几十米长坡度很大,人从上边站着滑下来,速度之快简直有些吓人,而下边围观的人更多,这里边就有一些很坏的家伙,当人从上边滑下来的时候,有人会偷偷的把脚伸出去,然后滑下来的人就会来一个空中转体七百二十度直挺挺落地。即使没人伸脚,也不知道当年出于什么目的,在滑梯的对面就是一道冰墙,如果不能及时减速,基本上人人都会撞到冰墙上去,所以那道冰墙上全是鼻血,血溅到冰上以后会非常非常的红,看的让人触目惊心。
等到我参加工作以后参与的冰灯制作规模就更大了,因为当时要求各大厂矿参与。这就好像打擂台了,每个冰景都有企业的说明和广告,这下子可成了大事了,每个工厂都调集人马,热火朝天的干冰灯。我们每天还享受补助费,而这补助费当时比我们工资还要高很多很多,所以能够去造冰灯没有点本事或者门路还真去不上呢。当时是一个木工厂负责雕塑,我们负责灯饰安装,那也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冰灯的建造过程:先在江面上取冰,工具也很原始,就是木工用的圆锯切割,然后用钩子勾上来运到现场,再凿成便于人力搬运的小块,两块冰之间的粘合直接用水就可以了,堆砌出大致的轮廓,木匠就用长柄的刨刃子开始雕刻。而我们就负责在冰槽里铺设导线和灯具。当时带队的是技术副队长,突然有一天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独立配置冰景区的配电盘,把我吓坏了,不过当时还很得意,这说明我技术过硬呗,于是人家在外边干活,我在电工房里配盘,当时还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电子元件,都是又大又蠢的接触器 互感器 中间继电器 时间继电器 瓷保险等等,缆线是35平方的铜线,我用了四五天的时间,外加被电击得象赵四一样的嘴角兴高采烈的请队长来验收,当队长看着噼啪作响的控制盘皱起了眉头,我都纳闷了。然后他盯着我问:你没配错吗?我当时就回答:我保证没配错,三十六条回路都是按设计时间设置的。队长叹了一口气拍着我肩膀说:兄弟,我为什么把这个活交给你?你看大家在外边冰天雪地的多辛苦啊,那点工资和补助费都吃吃喝喝了,拿什么给大伙搞福利呀?然后转身就出去了。我想了半天终于想明白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低着头当着全体同事的面对队长说:队长,我把盘配错了,所有的接触器都烧了,线也着了,这块盘整个废了。队长眼含着热泪安慰我说:没关系,年轻人肯用心就好,失败是成功他娘,我们大家都不会怪你的。其他同事也都喜上眉梢的安慰我,还主动过来给我敬酒。喝完了酒他们去干活,我回到电工房一通砸。收集了半电工兜的触点,骑车去找街上打银首饰的江浙人把触点都卖给了他们,他们看见我拿去的触点眼睛都快鼓出来了。然后回到电工房,把电工刀磨的飞快,一个下午把所有的缆线全部剥皮打捆,用倒骑驴推着送进了废品收购站。冰灯结束后,我们去哈尔滨玩了几天,回来以后又分了点钱,那个冬天真的很快乐。
当然冰雪带来的并不全是欢乐,我开车年头很多,事故率很低,少数的几次小事故基本都是在冬天里发生的。那时候的车也没有ABS,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就得听天由命。根本不受控制的车眼睁睁的就撞向别人的车,彼此都能看到对方惊恐的表情,然而又都无可奈何。最恐怖的一次是去满洲里的路上,那时候301国道非常窄,有的地方还有会车道。就是两台车根本不可能同时会车,必须是离会车道近的人退回去等人家过去了才能继续走。过十八拐的时候突然对面坡上冲下来一台拉原木的炮车。那狗东西根本也不减速,从大雪壳子里七八十公里的速度往下冲,我头发都立起来了,旁边已经没路可以躲了,心想这回这小命是交代在十八拐了。结果两车相会的时候,就看见对方驾驶员一脸轻松的打了一下方向盘,然后炮车扭了一个三节腰,妥妥的避开了我,后边的炮车其实已经快要冲出路面,但是又被惯性重新拖回了正道。等我下去停车以后,发现自己里边衣服都湿透了,手不停的哆嗦,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想冲着炮车方向骂一句都做不到了。
古时候有很多文人墨客赞美过北方的雪,近现代东北题材的作品也都离不开对雪的描述。冰雪对于东北人来说,就好像阳光空气一样存在的是那么自然,走在路上摔一个屁股蹲会骂这雪下个没完,冬天如果总不下雪又开始担忧开春会得病。那漫天的大雪飘在室外,却被东北人记挂在心头。没事会想起哥们喝醉了象动画片一样平平整整的扑倒在雪中,我们几个过去拿出手机一通拍,后来的赶来的时候人家要起来,结果用脚踩住继续拍。也会想起那次下大雪,男男女女几个人喝多了打雪仗,把雪团从一个女哥们的领口塞进去结果弄出来一个急性肾炎住院半个月。想起小时候在雪地里跋涉的口干舌燥,捏一个雪团边走边啃。记起了从外边装了一盆雪给深夜回家的大人搓手搓耳朵避免冻伤。最爱玩的是冬天坐通勤车的时候用手把玻璃上的冰融化做一个小脚丫的图案。最开心的是从街边地上摆着的一溜冰棍中找出自己最爱吃的那一种。北国的冰雪啊,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每年都有一半时间在冰雪中度过,这让东北人多了一些对于严酷环境的忍耐力和韧性。因为冰雪,我们想念春天,因为深秋,我们开始迎接冬季。对于东北人来说,冰雪就意味着希望,熬过去,就是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