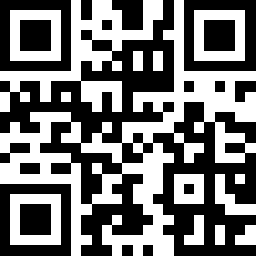乌鲁木齐情爱录—第49集
他顿了顿,开始了他的故事。
我的父亲是新疆一个有名的老画家,王总通过别人知道了我父亲,他们见过面之后,有所交往,但并不深。后来他想要求我父亲的一副画,但是他所要的是油画,因为他喜欢西洋油画,而我父母是画中国山水的,正好我父亲有个画家朋友,刚从美国进修回来,他是画油画的,知道吗?我见过他的画,那完全不符合一个老年画家的风格,因为那位老画家已经快八十岁了,很有梵高的感觉,就是那种《星月》一类的感觉,我也很喜欢他。我大哥自己有家公司,那位老画家不仅和我父亲关系好,也和我的大哥关系不错。一般来说,向人求画不是关系很好就是因为礼尚往来才可以求,因此王总向我父亲求画并不奇怪,我父亲很为难,给他吧,实在拿不出给的理由,不给吧,我父亲又无法碍于面子,而他不想去向那位老画家要一副送他。于是,我父亲就将这件事给我大哥说了,我大哥是个很讲义气的人,他关系复杂,朋友也多,就这样他出面去老画家那里拿了一副送给了王总。
按说,他们的交情到此也就结束,以后不会再有什么瓜葛,但是偏偏我大哥公司的一个员工不知道什么原因在上班时就死了,那个员工很年轻,25岁不到,男孩家里的父母就他一个孩子非要进行尸检查看原因是为了找公司赔偿问题。尸检很麻烦,要检查很多脏器,所以就要开腹,然后检查完毕再缝合上。尸检结果出来之后是病毒性心肌炎,医生的解释是劳累过度,也就是说,偶尔一次的感冒也会引起病毒性心肌炎,再加上劳累以至于发生心源性猝死,这下,死去的员工父母不干了,给我大哥两条路,坐牢或者赔偿一百万,他们把自己以后的养老钱都写进赔偿里了。
对于,我大哥来说,坐牢不可能,但是一百万对于一个公司来说也不是小数字,我大哥就找人,找来找去就找到了王总,王总在法院里有同学,然后由法院的同学调节,给那员工的父母赔了二十多万,当然我哥哥也给了他和他同学好处,具体是多少,我不知道,只是听我父亲说,这件事对我大哥来说躲过了一场劫难,算是拿钱消灾。本来这件事情到此也算完结了,但是,那个员工的父母因为思念孩子,对于赔偿本来就不满意,找人跟踪他,我哥哥也找了一帮社会上的人,就又打了架,又出了事。
讲到这里,拨鱼子说,这就是事情的经过。我说,怎么跟演电影是的,这是真事儿吗?拨鱼子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我家也一样。我问,那后来呢?你大哥现在呢?他说,好好的,当然这已经欠了王总的人情了,我说,钱不是都给了吗?怎么还欠?他说,不一样。怎么就不一样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不是这个理吗?他说,如果不求他帮忙的话,我哥哥也许现在还在牢里呢。我说,那画就白给了,可惜了。
拨鱼子,我觉得你怎么跟黑社会的一样,你到底是做什么的?他说,无业游民。我看着他说,你可得好好给我说,要不然,我得远离你,我不喜欢复杂的人,太麻烦,我没那么大胸怀。
我走过去掐着他的脖子一本正经地说,拨鱼子,今天我要知道关于对你的三个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痒死我了,他咯咯笑了起来,开始掰我的手,我说,不行,我今天就是要知道。他说,宝儿,你先把手松开,我快受不了了,真的,真的。他已经笑的快上气不接下气了。我放开了手。他一把把将我按在他身边。他说,你刚问的那三个问题,单位保安都会问,这是哲学问题我回答不了。
我看着他说,还有,你哥哥和王总之间的事情怎么他要说到你的头上呢?拨鱼子说,他只是想吓唬你远离我吧,虽说是他和我哥哥之间的事情,但是那毕竟是我哥。他将前面要问我的话题再次提了出来。
宝儿,回答我刚才的那个问题吧,你觉得他是个怎样的人。我说,给你说这些对他有什么危害吗?对你有什么好处吗?没有,但是,我得清楚你和他之间到底有什么牵连没有,我是在替你担心。
为了保险起见,也为了多个人陪在身边,我还是将我对王总的一点看法说给了拨鱼子。我说,说实话我对这个人不怎么了解,只知道他在对待女人的态度上含糊不清,拨鱼子问,什么叫含糊不清。我看他一眼,问那么清楚干什么?他说,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我无奈地说,目前在单位我就知道他和两个女人有关系,一个是秘书小美,一个是新来没多久然后又离开的小高的同学。
拨鱼子一直听着没有打断我。我说,他外形上挺有魅力的,但是单只说一点在对待女人的态度上我相信他会惹大麻烦的,当然我只是这样想想而已,现在的很多女人对待男人的态度就是你情我愿,互不干涉对方生活,也算是一种和谐的平衡关系,所以,王总应该是女人不断,还有,从这一点延伸出来的第二点,那可能就会跟钱有挂钩了。我的陈述完毕。拨鱼子问,宝儿,你没有拿过他的一分钱吧,我摇了摇头。他说,我就要你这句话,其余的我们也管不了。
在拨鱼子面前我不想对于王总有过多的疑问,但是想到后果我还是问了一句,后果会怎样?拨鱼子说,我不清楚,我不是警察也不是法官,但是有一句话,你必须要明白:多行不义必自毙!
我看着他没有出声。
天渐渐黑下来了,立春过去之后,白昼边长了,已经有了积雪融化的迹象,外面的白天也不是很冷,但是到晚上还是得赶紧钻进温暖的屋子里。
我站在拨鱼子的屋子里,走到阳台上向远处看去,他的屋子朝向不错,面向东方,直接可以看到博格达峰,城市暗下来,但是傍晚的夕阳在高空中还是留了点余晖洒在博格达峰上,有些许的金片散落在地上。
拨鱼子走过来,从背后抱着我,将手放在我的小腹上,然后就落在了两朵丰满的胸脯上。
我无动于衷,我说,拨鱼子,我不想自然与人的关系,一想,或者看到这样壮观的景象,我都会想到一种苍茫,一种宁静的慌乱,我会想到死。拨鱼子的嘴在我的颈项摸索,怎么会这样呢?知道么,去你家里,我觉得温暖极了,你的妈妈是一个具有天生艺术气质的人,我淡淡地问,此话怎讲?他说,你难道没有发现,她所说的每一句都是诗歌的语言吗?
我转过身来,窗外已经暗下来了。我们开始亲吻。吻一会停一会,像玩一种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一个人问一个人答,然后再互换角色。我一边挑逗他一边问,你妈妈好吗?我闭着眼睛不停在我脸上点着,我没有母亲。我们都停下了动作。我说,那你妈妈呢?他说,在我23岁那天他就去世了。为什么?什么原因?拨鱼子说,我们不要再待在阳台上了,有点冷。
我们进了卧室,躺在床上。和上次一样,四周很黑,很静。她是一位舞蹈演员,考了国家二级证,她非常喜欢跳舞,我还记得,她每次站在家里的窗台上压腿时总是让我半身躺在她的腿上,我们就聊天,我和她都喜欢这样时光。她是风湿性心脏病,很多很多年了,记得我小的时候她就开始犯病了,总是呼吸困难,嘴紫的很厉害,脚也肿,我半夜醒来她还靠在床头咳嗽,我的父亲从未离开过他半步,直到她去世之前。
我记得我前面给你说过,我两个哥哥的家庭和我父母的家庭都很不错,不仅仅是物质,还有家庭氛围与精神的,我的父母很相爱,他们给孩子留下了很好的榜样,所以我两个嫂子和我父母的关系都非常融洽。我轻轻地问他,生怕打断他的叙说,为什么你会叫他们为父亲母亲,你看我们都叫老爸老妈。他说,我不清楚,我从小一直这样叫过来的,因为我的哥哥们也是这样叫着的。我哦了一声。我说,你父亲现在在哪里?他现在依然住在幸福路的老干部休养所里,那里有他的画室,还有他和我母亲所有的回忆,我母亲的一只发卡,7年过去之后,还依然躺在他们的床头柜上,动都没动,我想,这就是我父亲对我母亲的爱吧。
他靠过来把脸埋进我的胸膛,我用手摸了摸,有潮湿的感觉,他哭了。我们在床上躺了很久,直到睡了过去。正在熟睡中,我的电话响了起来,我以为是家里的,但不是。
王总司机打来的。我看了时间已经快晚上一点了。我挂了电话,那边再打,我再次挂断,现在我害怕和他有任何联系,我怕有一天警察找到我的头上,那边发过来一条信息:我宁愿相信你不是落井下石的女人,但是没有证据证明我的猜测是毫无根据的。看到信息,我想,看来马总和拨鱼子说的没错,我关了机,但是又觉得有人仿佛要给我打进来电话一样让我不得不将电话打开。
拨鱼子还在卧室睡着,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一切都象是在梦中,我想到从朗朗在婚前的背叛开始,然后时间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如今这个盒子里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没有出现完毕,我还得面对,在不经意的时间里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