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刘万永:新闻作品都是遗憾的艺术
带着理想,能走得更远
——专访《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部副主任刘万永
张志安 刘虹岑
■个人简介
刘万永,1996年本科毕业于河北大学教育系,1998年毕业于中国新闻学院,同年进入《中国青年报》工作。现为特别报道部副主任,中共十八大代表。2003年全国新闻界抗击非典宣传优秀记者,中国青年报2010年“年度最佳记者”。曾三次获得中国新闻奖,并于2012年获得第十二届长江韬奋奖。代表作品有《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王佳俊冒名顶替读大学路线图》、《公安部处长洗冤录》等。
☐访谈实录
‘我是“官员的长相,记者的命”’
张志安、刘虹岑(以下简称“张志安”):你曾说自己做记者是“命不好,心态好”,为什么这么说?
刘万永:前两天,我们部门的人跟我开玩笑,说我是“官员的长相,记者的命”。我长得挺像官员的,但却是一条当记者的劳碌命。作为记者,很辛苦、收入比较低、工作没规律,当然也有风光的时刻和场合,但更多的时候面临着身体上的疲惫、心理上的压力以及持续降低的社会评价。
我觉得,现在整个社会对记者的评价越来越低。八十年代的时候,记者承担了更多社会启蒙的作用,《人民日报》的记者去各地采访,都会被当成是“领导”,受人尊敬。但现在,大家更多地是把记者的工作与低俗新闻、为了出名而制造假新闻联系在一起。
张志安:80年代记者不仅在启蒙,而且也在宣传。现在大家在抱怨炒作或假新闻,但这个职业是不是也被祛魅,告别了宣传者、启蒙者的角色回归了记录者的本位呢?
刘万永:记者的职责当然是记录历史,从说教、宣传到记录,确实回归了媒体工作的本位。我不认为把过去记者当成领导是对的,但记者这个行业社会评价持续降低,确实让我很忧心。
张志安:在“命不好”的情况下,你怎么保持比较好的心态呢?
刘万永:如果前提是“命不好”,你可以离开,也可以选择留下来。如果选择后者,就努力有一个好的心态。
做记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个行业,热爱自己的工作。
一方面,从判断选题到最终成稿这个过程中,记者是否有用心,对这个稿子的成败影响是很大的。虽然稿子写出来,有时候读者看不出来记者是否用了心,但是记者自己肯定知道。
另一方面,从收入、社会地位、社会声誉上来讲,有很多工作比记者这个工作来得好。所以,我觉得一个记者是否能够走得够远,是事关新闻理想的。我在《做有硬度的新闻》[1]这篇文章中写道,有很多人因为各种因素而离开了新闻这一行,我并不反对别人这么做,这是件好事,说明这个人还是有很多能力,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的职业。但新闻这个行业还是应该有人能够坚持下去。一个学新闻的人,毕业之后在这个行业干个三五年,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有的人能够坚持下去,而且还奋斗在一线,这是值得尊重的。
对于我而言,我喜欢并且能够胜任这个工作,至于其它因素,比如收入,我不是不考虑,只是我现在的收入自己能够接受,而且这个工作还能给我带来很多乐趣,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带着新闻理想,在这条路上能够走得更远一点。
张志安:为什么不少记者到你这个年龄,都容易感到倦怠甚至厌烦,但在你同事的眼中,你还是保持着非常积极的状态。你是如何克服职业疲惫感的?
刘万永:疲惫感肯定大家都有,我不可能像打了鸡血一样,永远不疲惫。懈怠的时候,有时也会问自己:岂有豪情似旧时?!只是我对新闻还有热情。我一直觉得,还没有做到我理想的那个状态。
我在采访中心当记者的时候,觉得要是能在“冰点”这个版面上发一篇稿子,那我在离开《中国青年报》时肯定不会有遗憾了。但是2004年的时候,我就成为了“冰点”的记者,那发稿子是我的工作了,这个想法也就烟消云散了。
张志安:你心中那个理想的状态是怎样的?
刘万永:这个理想状态,我不能很精确地描述出来,只能说是我对自己的期望吧。“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一篇稿子再好,也会有缺憾的。写出好稿子,也许永远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张志安:你一直对做事件性的报道选题比较感兴趣。到了现在这个年龄,还会有那种被一个选题“击中”的感觉吗?
刘万永:应该还是有的。前年年底的时候,我们特别报道部碰到了一个选题,是一个兰州大学的学生发帖举报自己的同学公务员考试作弊的事[2],我们连着发了3个整版。虽然已经年底了,但我们部门所有的人都特别兴奋,我们主任说“这帮人个个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对于我们而言,从年初到年末,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稿子也是一版一版地出……当真正遇到好的题目的时候,大家都会非常兴奋,都会有一种职业冲动。
我到这个部门已经有7年了,一直到现在,遇到好题目都会有一种冲动,想要自己去采访。前几天,我在微博上偶然知道原《中国电子报》副总编羁常林锋押六年被判无罪的事情[3]:宣判无罪后,常林锋举着严重变形的双手,称遭受了刑讯逼供。
我当时在家,立刻就联系发微博的人,他是我的师弟,告诉我北京媒体都不能做这个选题。我想,我一定要做这个选题,于是就立刻开始找律师、找判决书,然后把稿子写了出来。本来这个稿子,我不写也没事,也可以找别的记者来写,但我还是有这股冲动,这股冲动是非常宝贵的。
如果一个记者遇到新闻时都没有反应,那我认为他已经到了离开这个行业的时候了。
张志安:到了你这个年龄,还能有这种对新闻的冲动,确实很不容易。不知道你怎么看现在自己带的年轻记者和实习生,他们对于新闻的看法与你们那一代调查记者相比有什么不同吗?
刘万永:每次跟他们接触,都能学到很多东西。很多实习生受到的专业教育都特别好,关于怎么用互联网、怎么做视频方面,比我们都擅长许多。
有很多我认识的年轻记者,他们接受信息的能力、搜集和整合信息的能力也非常强,但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积累经验、磨练做新闻的技巧。他们写稿子,写个两三年,就不愿意再去锤炼了。这与我们当年不太一样。
做记者,当然会有一些个人的天赋在里面,因为这些东西的实践性很强。但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积累经验的。如果一个记者愿意花三五年的时间去磨练自己,那么他肯定比刚入行的时候写稿子更成熟。但是,越来越少的年轻记者愿意投入三五年的时间去做这些事情,认为自己花两三年就可以了,大概他们觉得以自己的能力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掌握这些东西了吧。
张志安:你带过的实习生当中坚定要做记者的人多吗?
刘万永:我们部门的实习生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经过实习,坚定不做记者了,因为觉得当记者太累了;另一类是经过实习,坚定了做记者的决心,认为当记者非常好,很有成就感,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至于说这个工作吃苦受累、挣钱少,他们根本不在乎,至少在一定时间内是不在乎的。
我们部门曾经有一个女实习生,被保送到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读研究生。面试的时候,老师问她一个问题:“你本科是学新闻的,为什么硕士要学社会学呢?”她回答说:“我是为了自己将来能更好地成为一个记者。”她还是觉得,做记者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是一件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个记者,心态好就不要期望太高’
张志安:你2004年7月进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2005年改跑教育报道,2007年又转入特别报道部。这三段不同的工作经历,带给你的体验和收获有什么不同?
刘万永:刚到“冰点”的时候,我发现新闻其实不是我们原来做的那个样子。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写人物稿,被编辑退回了3次。时任“冰点”主编、现中青报副主编杜涌涛告诉我说:“你一定要放下架子,不要以为自己是一个成熟的记者。”我说:“我哪有什么架子啊,我确实是不知道你们想要什么!”改到第四遍的时候,杜涌涛说:“你不用改了,再改还是这个样子,无非是加一段,减一段而已。”
后来,他重新改写,稿子突然有了脱胎换骨的感觉,就像一个小姑娘,你在她四五岁的时候见过她,等她十八岁的时候,你再一看,完全是“女大十八变”,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离开“冰点”不是我自己主动提出的,但我在“冰点”的时候确实压力特别大。从年龄上来讲,有比我大的、成熟的记者,也有比我小的、写稿子很猛的年轻记者。年轻记者没有什么惯性,上手很快,但是我需要把过去已经成型的套路改掉,要重新按照“冰点”的路数去写。
张志安:在你看来,“冰点”的特稿和特别报道部的调查性报道各有什么特点?
刘万永:特稿更讲究文章的节奏感和可读性,调查性报道更需要逻辑性,但是这两种稿子确实都需要把稿子写得吸引人。
我也比较困惑的是,调查性报道可读性比较差,很难写得生动,因为要生动就需要很多细节,但如果有一些生动的细节我没有证据来证明,只好宁可放弃。此外,在逻辑性和可读性之间,怎么平衡,怎么达到最佳也是我比较困惑的问题。
张志安: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青年报》是引领深度报道的前沿阵地,在年轻人中影响很大。现在,随着受众阅读习惯的改变、社会和媒介环境的变化,这份报纸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有所衰减。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万永:如果一些青年读者不喜欢《中国青年报》了,除了获得信息的渠道多元这个因素之外,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中国青年报》作为一份青年报,为什么青年不喜欢。也许是我们报道的内容有问题,或者是语言风格有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思考。
张志安:你长期做舆论监督报道,过去这么多年,你对舆论监督的空间和环境变化是怎么看的?此外,有没有感觉监督报道越来越难以实质性的解决问题?
刘万永:我觉得舆论监督的空间有时候宽松、有时候紧张,总体来讲应该是在好转了吧。
具体说到报道效果,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过去,《焦点访谈》7点38分播节目,当地政府连夜开会把相关负责人都免掉,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的记者不要给自己加那么多额外的期待,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报道,至于说报道之后能起到什么作用,并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也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
张志安:调查记者比较容易有英雄主义情怀,希望通过调查性报道去推动和影响现实。在你看来,记者是否应该有通过报道来改变社会的使命感呢?
刘万永:我觉得记者能够通过报道来推动社会进步是一件好事,有这个期望也是很正常的,但是不要期望太高。如果期望太高就容易变得很沮丧,无力感就会加强,虚无感也会越来越强。当虚无感越来越强烈的时候就会考虑离开这个行业了。一个记者,心态好就是不要期望太高。
张志安:这方面,你的心态看起来很平和。你的同事叶铁桥告诉我们:“特别报道部的调查性报道就是一个拳头,如果这个拳头没打痛对方,我们就会觉得沮丧。”你会有这种沮丧的感觉吗?如果报道出来后产生的影响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你会如何调整心态呢?
刘万永:没有,很正常啊;有,是额外的嘛。我做了15年的记者了,大家能记住的我写的报道无非也就那一两篇,实际上我做的很多报道,大家根本没有听说过。如果今天我们的报道出来了,没有达到效果,这是很正常的,每天有那么多的报道,我们的报道也许淹没在众多的报道中了。
所以,没有是正常的,有是意外的收获。要是有了这种心态,记者在做稿子的过程中就会心态很平和。
张志安:其实,说一件事或一篇报道影响一个人,经常是比较牵强的。但我们还是想知道,你当记者15年来,有没有一件事或者一篇报道使你对记者这个职业的认识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刘万永:我最早做教育新闻,后来写一些法制新闻,现在主要是做舆论监督式调查性报道。这些年的从业过程中,我感觉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过去,我们挖到一个料,拿到一些证据,就会认为自己挖到了真相,我们拿到的东西就是事实的全部;但现在,说到真相的时候,会越来越沉重,越来越慎重,我们不敢轻易说我们拿到了真相的全部。
2008年,我写过一篇稿子《谁盗卖了季羡林的藏品》[4]。当时根据事件多方提供的书面证据、视频等等,就会得出一个看似毫无疑问的结论。但是,这个结论其实是错误的。事后证明,这里面只有一个人提供的视频是真的,其他人都在说谎。不过,幸亏当时我在写每一个人的话的时候都标明了消息源,对他们的话都有所保留,没有用肯定的、确切的语气去叙述,而且也没有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虽然稿子出来有一定影响,但是我没有成为被告。这个事情对我的教训是非常深的。记者永远不要在采访中天然地认为,我掌握的就是一个多么严谨的证据链,或者是一个多么全面的真相。
看过本文的人还看过
暂时没有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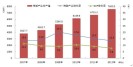







新浪警示:任何收费预测彩票会员等广告皆为诈骗,请勿上当!点击进入详情